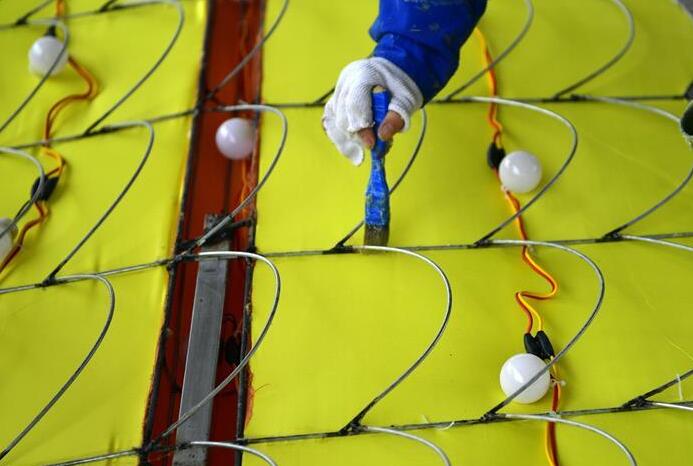蘇東坡買來了一頭牛,還有鋤頭、水桶、鐮刀之類的農具,那是一個農民的筆墨紙硯,收納着他的時光與命運。勞作時,蘇東坡頭戴竹笠,在田間揮汗。第一年種下的麥子在時光中發育,不斷抬高他的視線,讓他對未來的每一天都懷有樂觀的想象。孔孟老莊、四書五經,此時都沒了用場。他日復一日地觀賞着眼前的天然大書,對它在每個瞬間裏的細微變化深感癡迷。
人生如蟻,他不是“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為五斗米折腰。
一
公元1082年,被稱為“天下行書第三”的《寒食帖》,在黃州,等着蘇軾書寫。
“天下行書第一”,是王羲之的《蘭亭集序》,寫於東晉永和九年(公元353年)。
四百年後,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顏真卿寫下“天下行書第二”——《祭侄文稿》。
在我看來,被稱作“天下行書第二”的,應該是李白《上陽&帖》。當然,這只是出於個人偏好。藝術沒有第一名,《蘭亭集序》的榜首位置,想必與唐太宗李世民的推崇有關,但假如它永遠第一,後來的藝術史就沒有價值了,後來的藝術家就都可以洗洗睡了。
當然我們也不必那麼較真,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第一。
無論怎樣,《寒食帖》,這“天下行書第三”,要等到《祭侄文稿》三百多年之後,才在蘇軾的筆下,恣性揮灑。
王羲之《蘭亭集序》原稿已失,故宮博物院收藏的,是唐代虞世南、褚遂良的臨本和馮承素的摹本,&&故宮博物院亦藏有褚遂良臨絹本和定武本。
顏真卿《祭侄文稿》和蘇軾《寒食帖》,則都保存在&&故宮博物院。
在《祭侄文稿》和《寒食帖》之間,有五代楊凝式,以超逸的書美境界獲得了顯著的歷史地位;有梅妻鶴子的林逋,書法如秋水明月,乾淨透澈,一塵不染;有范仲淹,“落筆痛快沉着”。他們的作品,故宮博物院都有收存。其中范仲淹的楷書《道服讚》,筆法瘦硬方正,民國四公子之一的張伯駒先生説它“行筆瘦勁,風骨峭拔如其人”,《遠行帖》和《邊事帖》,一律粉花箋本,亦在清勁中見法度,一如他的人格,“莊嚴清澈,信如其品”。
但宋代書法的真正代表,卻是“蘇黃米蔡”。蘇軾《寒食帖》,則被認為是宋人美學的最佳範例。
這幅字,是在一個原本與蘇軾毫無干係的地方——黃州完成的。也是在這一年,蘇軾寫下了《念奴嬌·赤壁懷古》《赤壁賦》和《後赤壁賦》。
這字,這詞,這文,無不成為中國藝術史上的不朽經典。
將近一千年後,我在書房裏臨寫《寒食帖》,心裏想著,公元1082年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年份;在這一年,蘇軾的生命裏,到底發生了什麼?
二
11世紀,那個慷慨收留了蘇軾的黃州,實際上還是一片蕭索之地。這座位於大江之湄的小城,距武漢市僅需一個小時車程,如今早已是滿眼繁華,而在當時,卻十分寥落荒涼。
蘇軾在兒子蘇邁的陪伴下,一路風塵、踉踉蹌蹌地到了黃州——一個原本與他八竿子打不着的荒僻之地。那時的他,一身鮮血,遍體鱗傷。烏&詩獄,讓他領教了那個朝代的黑暗。所幸,他沒有被推上斷頭&。黃州雖遠,畢竟給了他一個喘息的機會,讓他慢慢適應眼前的黑暗。他的入獄,固然是小人們精誠合作的結果,但不能説與他自己沒有干系。那時的他,年輕氣盛,對劣行從不妥協,在他的心裏,一切都是黑白分明,但對於對方,他無可奈何,自己,卻落了一堆把柄,所謂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他喜歡寫詩,喜歡在詩裏發牢騷,他不懂“墻裏鞦韆墻外道”的道理,説到底,是他的生命沒有成熟。那成熟不是圓滑,而是接納。黑暗與苦難,不是在旦夕之間可以掃除的,在消失之前,他要接納它們,承認它們的存在,甚至學會與它們共處。
那段時間,蘇軾開始整理自己複雜的心緒。蔣勳説:“這段時間是蘇軾最難過、最辛苦、最悲劇的時候,同時也是他生命最領悟、最超越、最昇華的時候。”
人是有適應性的,他開始適應,而且必須適應這裡的生活。
從蘇軾寫給王慶源的信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黃州最初的行跡:
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客至,多辭以不在,往來書疏如山,不復答也。此味甚佳,生來未曾有此適。
在給畢仲舉的信中,又説:
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安在哉?
到了黃州,蘇軾父子一時無處落腳,只好在一處寺院裏暫居。那座寺院,叫定惠院,坐落在城中,東行五十步就是城墻的東門,雖幾度興廢,但至今仍在。院中有花木修竹,園池風景,一切都宛如蘇軾詩中所言。只是增加了後世仰慕者的題字匾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是晚清名臣林則徐寫下的一副對聯:嶺海答傳書,七百年佛地因緣,不僅高樓鄰白傅;岷峨回遠夢,四千里仙蹤游戲,尚留名剎配黃州。
蘇軾寓居定惠院之東,抬眼,見雜花滿山,竟有海棠一株。海棠是蘇軾故鄉的名貴花卉,別地向無此花,像黃州這樣偏遠之地,沒有人知道它的名貴。看見那株海棠,蘇軾突然生出一種奇幻的感覺。他抬首望天,心想一定是天上的鴻鵠把花種帶到了黃州。那株茂盛而孤獨的繁華,讓他瞬間看到了自己。他慘然一笑,吟出一首詩:
江城地瘴蕃草木,唯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忽逢絕艷照衰朽,嘆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致,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樽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當年唐玄宗李隆基在沉香亭召見楊貴妃,貴妃宿醉未醒,玄宗見她“朱唇酒暈”,笑曰:“豈是妃子醉耶?真海棠睡未足耳。”唐玄宗以人比花,蘇軾則是以花自寓了。
初到黃州的日子裏,他沒事就抄寫這首詩,不知不覺之間,竟然抄寫了幾十本。
獨自走路,在這無人問候的小城,沒有朋友,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只有一株遠遠的花樹,與他相依為伴。這個倉皇疲憊的旅者,願意像楊貴妃那樣,宿醉不醒。竹葉在定惠院綿密的風聲中晃動着,蘇軾沉沉地睡去,像他詩裏寫的:
畏蛇不下榻,睡足吾無求。
醒來時,窗外依舊是綿密的風聲,還夾雜着竹子的清香。於是他覺得,這巢穴雖小,卻是那樣地溫暖。蕭蕭的風聲中,他再次睡去,“昏昏覺還臥,輾轉無由足”,但沒有做夢。即使做夢,也不會夢到朝廷上的歲月,那歲月已經太遠,已被他甩在身後,丟在千里外的皇城中。
但有時也有夢。他會夢見故人,夢見自己的父親、弟弟,夢見司馬光、張方平,甚至夢見王安石。這讓他在夢醒時分感到一種徹骨的孤寂。這裡遠離朝闕,朋友都遠在他鄉,找不出一個可以交談的人,連敵人都沒有。
寂寞中的孤獨者,是他此時唯一確定的身份。
在定惠院寓居,他寫下一首《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他會在萬籟俱寂時刻,漫步於修竹古木之間,諦聽風聲雨聲蟲鳴聲,也有時去江邊,撿上一堆石子,獨自在江面上打水漂。還有時,他乾脆跑到田間、水畔、山野、集市,追着農民、漁父、樵夫、商販談天説笑,偶爾碰上不善言辭的人,無話可説,他就央告人家給他講個鬼故事,那人或許還要推辭,搖頭説:“沒有鬼故事。”蘇軾則説:“瞎編一個也行!”
話落處,揚起一片笑聲。
三
花開花落,風月無邊,可以撫慰腦子,卻不能安撫肚子。蘇軾的俸祿,此時已微薄得可憐。身為謫放官員,朝廷只提供一點微薄的實物配給,正常的俸祿都停止了。而蘇軾雖然為官已二十多年,但如他自己所説,“俸入所得,隨手輒盡”,是名副其實的“月光族”,並無多少積蓄。按照黃州當時的物價水平,一斗米大約二十文錢,一匹絹大約一千二百文錢,再加上各種雜七雜八的花銷,一個月下來也得四千多文錢。對於蘇軾來説,無疑是一筆鉅款。更何況,他的家眷也來到黃州相聚,全家團圓的興奮過後,一個無比殘酷的現實橫在他們面前:這麼多張嘴,拿什麼糊口?
為了把日子過下去,蘇軾決定實行計劃經濟:月初,他拿出四千五百錢分作三十份,一份份地懸挂在房樑上。每天早晨,他用叉子挑一份下來,然後藏起叉子,即便一百五十錢不夠用,也不再取。一旦有節余,便放進一隻竹筒。等到竹筒裏的錢足夠多時,他就邀約朋友,或是和夫人王閏之以及侍妾王朝雲沽酒共飲。
即使維持着這種最低標準的生活,蘇軾帶到黃州的錢款,大概也只能支撐一年。一年以後該怎麼辦?妻子憂心忡忡,朋友也跟着着急,只有蘇軾淡定如常,説:“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意思是,等錢用光了再作籌劃,正所謂水到渠成,無須提前發愁,更不需要提前預支煩惱。
等到第二年,家中的銀子即將用盡的時候,生計的問題真的有了解決的辦法。那時,已經是春暖時節,山谷裏的杜鵑花一簇一簇開得耀眼,蘇軾穿着單薄的春衫,一眼看見了黃州城東那片荒蕪的坡地。
馬夢得最先發現了那片荒蕪的山坡。他是蘇軾在汴京時最好的朋友之一,曾在太學裏做官,只因蘇軾在他書齋的墻壁上題了一首杜甫的詩《秋雨嘆》,受到圍攻,一氣之下他辭了官,鐵心追隨蘇軾。蘇軾到黃州,他也千里迢迢趕來,與蘇軾同甘共苦。
馬夢得向官府請領了這塊地,蘇軾從此像魯濱遜一樣,開始荒野求生。
那是一片被荒置的野地,大約百餘步長短,很久以前,這裡曾經做過營地。幾十年後,曾經拜相(參知政事)的南宋詩人范成大來黃州拜謁東坡,後來在《吳船錄》裏,他描述了東坡的景象:
郡東山壟重復,中有平地,四向皆有小岡環之。
那片被荒棄的土地,蘇軾卻對它一見傾心,就像一個飢餓的人,不會對食物太過挑剔。這本是一塊無名高地,因為它位於城東,讓蘇軾想起他心儀的詩人白居易當年貶謫到忠州做刺史時,也居住在城東,寫了《東坡種花二首》,還寫了一首《步東坡》,所以,蘇軾乾脆把這塊地,稱為“東坡”。
他也從此自稱“東坡居士”。
中國文學史和藝術史裏大名鼎鼎的蘇軾,此時才算正式出場。
四
蘇東坡不會忘記那一年——宋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他在那塊名叫東坡的土地上開始嘗試做一個農民。
蘇東坡開始農業生産的第一個動作,應該是“煽風點火”,因為那些枯草,枝枝柯柯,彎彎曲曲,纏繞在土地上,拒絕着莊稼生長,蘇東坡覺得既刺手,又棘手。於是,蘇東坡在荒原上點了一把火。今天我們想象他當時呼喊與奔跑的樣子,內心都會感到暢快。因為他不只燒去了地上的雜草,也燒去了他心裏的雜草。自那一刻起,他不再患得患失,而是開始務實地面對自己生命中的所有困頓,他懂得了自己無論站立在哪,都應當從腳下的土壤中汲取營養。火在荒原上燃起來,像有一支畫筆,塗改了大地上的景物。大火將盡時,露出來的不僅是滿目瓦礫,竟然還有一口暗井。那是來自上天的犒賞,幫助他解決了灌溉的問題。這讓蘇東坡大喜過望,説:“一飽未敢期,瓢飲已可必!”那意思是,吃飽肚子還是奢望,但是至少,不必為水源發愁了。
蘇東坡買來了一頭牛,還有鋤頭、水桶、鐮刀之類的農具,那是一個農民的筆墨紙硯,收納着他的時光與命運。勞作時,蘇東坡頭戴竹笠,在田間揮汗。第一年種下的麥子在時光中發育,不斷抬高他的視線,讓他對未來的每一天都懷有樂觀的想象。孔孟老莊、四書五經,此時都沒了用場。他日復一日地觀賞着眼前的天然大書,對它在每個瞬間裏的細微變化深感癡迷。
我們沒有必要把蘇東坡的那段耕作生涯過於審美化,像陶淵明所寫,“晨興理荒穢,戴月荷鋤歸”,因為對於蘇東坡本人來説,他的所有努力都不是為了審美,而是為了求生。我從小在城市里長大,不曾體驗過稼穡之苦,也沒有在廣闊天地裏練過紅心,但我相信,農民是世界上最艱苦的職業之一。對蘇東坡而言,這艱辛是具體的,甚至比官場還要牢固地控制着他的身體。他不是“不為五斗米折腰”,而是天天要為五斗米折腰,折得他想直都直不起來。
但他是對土地折腰,不是對官場折腰。相比之下,還是對土地折腰好些——當他從田野裏直起身,他的腰身可以站得像樹榦一樣筆直,而在官場上,他的腰每時每刻都是彎的,即使睡覺、做夢,那腰也是彎的。李公麟《孝經圖》卷中的這個細節,就是對這一身體命運的生動記錄。一個人生下來,原本是健康的,但官場會把他培養成殘疾人——身體與精神的雙重殘疾,死無全屍,因為在死後,他的靈魂也是彎曲的。
土地是講理的,它至少會承認一個人的付出,一分耕耘,幾分收穫。
他的勞動生涯再苦再累,他的心是自由的。土地徵用了他的身體,卻使他的精神得到了自由。在這裡,他無須蠅營狗茍、茍且偷安。官場培養表演藝術家,他們臉上可以變換出無數種表情,但沒有一種表情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他們都是演技派,而蘇東坡是本色派,他不會裝,也裝不像——他的表演課永遠及不了格。官場上絕大多數官員都會認為,這世界上什麼都可以丟,唯獨官位不能丟;而對於蘇東坡來説則剛好相反,如果這個世界一定要從他身上剝奪什麼,那就把官位拿去吧,剩下的一切,他都捨不得丟掉。
蘇東坡站在烈日下的麥田裏,成了麥田裏的守望者,日復一日地經受着風吹和日曬,人變得又黑又瘦。他的臂膀和雙腿,從來也沒有像這樣酸脹,從酸脹轉為腫痛,又從腫痛轉為了麻木。而他的情緒,也由屈辱、悲憤,轉化為平淡,甚至喜悅。那喜悅是麥田帶給他的——那一年,湖北大旱,幸運的是,蘇東坡種的麥子,長勢旺盛,芒種一過,麥子就已成熟。
這是田野上最動人的時刻,蘇東坡一家在風起雲涌的麥田裏,搶收麥子。他讓妻子用小麥與小米摻雜,將生米做成熟飯。他吃得香,只是孩子們覺得難以下咽,説是在“嚼虱子”,夫人王閏之則把它稱作“新鮮二紅飯”。
但蘇東坡心中的自我滿足是無法形容的,因為他經歷了一次神奇的萃取,用他艱辛而誠實的勞動,把大自然的精華萃取出來。
一個黃昏裏,他從田裏返回住處。吱呀一聲,沉重的門被推開了。樸素的農舍裏沒有太多的東西,只有簡易的床榻,有吃飯和讀書兼顧的桌子,有長長的木櫃放在地上,上面或許擺放着一面女人用來梳粧的鏡子——那是唯一可以美化他們的事物。太陽的余光從屋檐的齒邊斜射進窗格,一些灰塵的微粒在方形的光中飄動,證明屋子裏的空氣不是絕對靜止。生活是那樣自然而然,他好像與生俱來,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場景中。繁華的汴京、皇宮、朝廷,好像都是不切實際的夢。這裡似乎只有季節,卻看不見具體的日子。但他並不失望,因為季節的輪迴裏,就蘊藏着未來的希望,這是至關重要的。
獨自啜飲幾杯薄酒,晃動的燈影,映照出一張瘦長的臉。
蘇東坡提起筆,將筆尖在硯&上掭得越來越細,然後神態安然地,給朋友們寫信。這段時間,為他留下最多文字的就是書信尺牘。他説:“我現在在東坡種稻,雖然勞苦,卻也有快樂。我有屋五間,果樹和蔬菜十余畦,桑樹一百餘棵,我耕田妻養蠶,靠自己的勞動過日子。”
後來,老友李常任淮南西路提刑,居官安徽霍山,聽説蘇東坡在耕田糊口,就給他帶來了一批柑橘樹苗。這讓他沉醉在《楚辭》“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的燦爛辭句裏。他在詩裏自嘲:“饑寒未知免,已作太飽計。”
假如我們能夠於公元1082年在黃州與蘇東坡相遇,這個男人的面容一定會讓我們吃驚——他不再是二十年前初入汴京的那個單純俊美的少年,也不像三年前離開御史&監獄時那樣面色憔悴蒼白,此時的蘇東坡,瘦硬如雕塑,面色如銅,兩鬢皆白,以至於假若他在夢裏還鄉,從前的髮妻都會認不出他來,此時的他,早已“塵滿面,鬢如霜”。
有一天夜晚,蘇東坡坐在燈下,看見墻壁上的瘦影,自己竟悚然一驚。他沒有想到自己已經瘦成這個樣子。他趕忙叫人來畫,只要他畫輪廓,不要畫五官。畫稿完成時,每個人都説像,只看輪廓,就知道這是蘇東坡。
五
似乎一切都回到了原點。蘇東坡原本就出身於農家,假如他不曾離家,不曾入朝,不曾少年得志,在官場與文場兩條戰線上盡得風流,他或許會在故鄉眉州繼承祖業,去經營自家的土地,最多成為一個有文化的勞動者。此時,他在官場上轉了一圈,結局還是回到土地上,做一介農夫。
好像一切都不曾開始,就已結束。
但他不是一個普通的農夫。對於一個農夫來説,田野家園,構成了他全部的精神世界,而對蘇東坡來説,田野即使大面積地控制了他的視線,在他的心裏也只佔了一個角落。他的心裏還有詩,有夢,有一個更加深厚和廣闊的精神空間等待他去完成。他的精神半徑是無限的。
我想那時,不安和痛苦仍然會時時襲來。那是文墨荒疏帶來的荒涼感,對於蘇東坡這樣的文人,“會引起一種特殊的飢餓感”。每當夜裏,蘇東坡一個人靜下來,他的心底便會幽幽地想起一個人。他從來沒有見過那個人,但在蘇東坡的案頭,那人的詩集翻開着,蘇東坡偶爾閒暇,便會讀上幾句。讀詩與寫詩,其實都是一個選定自我的過程。一個人,喜歡什麼樣的詩,他自己就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公元4世紀的東晉,有一個詩人,曾經當過江州祭酒、建威參軍、鎮軍參軍、彭澤縣令。但這一串威赫的名聲拴不住他的心,終於,他當彭澤縣令八十多天,便棄職而去,歸隱在鄱陽湖邊一個名叫斜川的地方,寫下《歸園田居》這些詩歌,和《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歸去來兮辭》這些不朽的散文。
陶淵明的名字,對中國人來説早就如雷貫耳,在蘇東坡的時代亦不例外。那段時光裏,陶淵明成了蘇東坡最好的對話者。他説:“淵明詩初視若散緩,熟讀有奇趣。如‘曖曖遠人村,依依墟裏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又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大率才高意遠,則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運斤,無斧鑿痕,不知者則疲精力,至死不悟。”
時間把這兩位不同時代的詩人越推越遠,但在蘇東坡的心裏,他們越來越近。或許,只有在黃州,在此際,蘇東坡才能如此深入地進入陶淵明的內心。蘇東坡喜歡陶淵明,是因為他並不純然為了避世才遁入山林,而是抱着一種審美的態度,來重塑自己的人生。他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他也不是避世,而是入世,只不過這個“世”,不同於那個“世”。在陶淵明心裏,這個“世”更加真實、豐沛和生動,風日流麗、魚躍鳶飛、一窗梅影、一棹扁舟,都蘊含着人生中不能錯過的美。生命就像樹枝上一枚已熟軟的杏子,剝開果皮,果肉流動的汁液鮮活芳香,散發着陽光的熱度。陶淵明要把它吃下去,而不是永遠看著它,事不關己,高高挂起。這位田野裏質樸無華的農民,不僅開闢了中國山水文學之美,也成就了中國士大夫人生與人格之美,讓自然、生活與人,彼此相合。
七個世紀以後,在黃州,在人間最孤寂的角落,蘇東坡真正讀懂了陶淵明,就像兩片隔了無數個季節的葉子,隔着幾百年的風雨,卻脈絡相通,紋路相合。張煒説:“他們都是&&‘叢林’(指官場叢林)之人,都是身處絕境之人,都是痛不欲生之人,都是矛盾重重之人,都是愛酒、愛詩、愛書、愛友人、愛自然之人。”蘇東坡一遍遍地抄寫《歸去來兮辭》。時至今日,我在&&故宮博物院打量這件手稿原跡,仍見濕潤沖淡之氣在往昔書墨之間流動回轉。那是他在書寫自己的前世——他在詞裏説:“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寫字的時候,他就成了陶淵明,而黃州東坡,就是昔日的斜川。
清末民初大學者王國維在《文學小言》中寫道:
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
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性,始能産生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子美、子瞻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
自夏商周三代以下,浩瀚數千年,王國維只篩選出四個人,分別是:屈原、陶淵明、杜甫、蘇東坡。而這四個人,幾乎全部集中在上一個一千年,也就是公元前340年(屈原出生)到公元1101年(蘇東坡去世),此後近一千年(12世紀到20世紀),一個名額也沒佔上。
假如從這四者中再選,我獨選蘇東坡,因為蘇東坡身處的宋代,中國歷史正處於一場前所未有的變遷中,機遇更多,困境也更多,尤其對於蘇東坡這樣的人,幾乎是冰炭同爐。蘇東坡就是宋代這只爐子裏冶煉出來的金丹,他在精神世界裏創造的奇蹟,既空前,也絕後。但他不是橫空出世的,有人以自己的生命和藝術實踐為他做了歷史的輔墊,那個人就是陶淵明。
(本文摘自《在故宮尋找蘇東坡》,祝勇著,浦睿文化出品,湖南美術出版社2017年7月第一版,定價:7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嬋整理)

-
佛係青年,該走心的時候也得走心
2017-12-16 10:16:11
-
是誰製造了微信朋友圈裏的“關懷式”謠言?
2017-12-16 10:16:11
-
全球電子垃圾回收率僅20% 對人類環境造成威脅
2017-12-16 10:16:11
-
專家預測:今年冬天是冷是暖?
2017-12-16 10:16:11
-
徵集丨2018"我向總理説句話"網民建言
2017-12-15 09:39: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