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如憐取眼前人”,更拓詞中意境新
晏殊詞中的理性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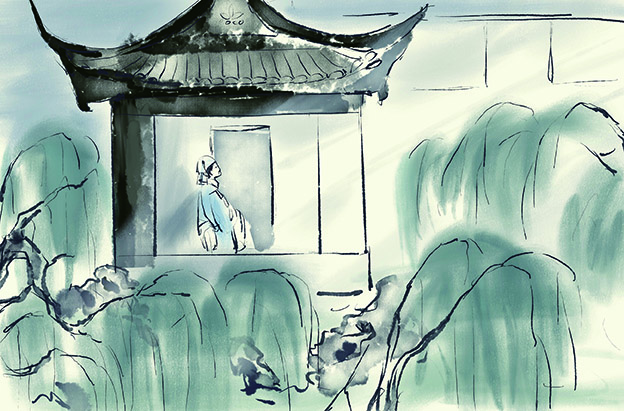
製圖:何嘉悅
葉嘉瑩講授
陸有富整理 於家慧審校
晏殊詞有慰藉的辦法
晏殊的《浣溪沙》:
一向年光有限身,等閒離別易銷魂。酒筵歌席莫辭頻。
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很多人考到50多歲才考中進士,比如韋莊;而晏殊是幸運的,14歲就被賜同進士出身,後來官至秘書省正字。不管是仕途上幸運的人,還是仕途上不幸的人,不管是理性的詩人,還是純情的詩人,都有我們人類所共有的無常的悲哀。無論你是什麼樣的人,即使你富貴顯達,貴為天子,也不能夠避免人生的短暫和無常。還有一種離別的悲哀,也是天下人都必須經歷的。生離死別的悲哀是我們人類共同的、最基本的感情。《古詩十九首》之所以奇妙,是因為它所寫的都是我們人類最基本的感情,無常的悲哀、離別的悲哀、追求不得滿足的悲哀。
可是對待這種無常和離別,每個人的反應都不一樣。李后主寫“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是無常,“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是離別,他得出的結論是“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其實晏殊所寫的基本感情是一樣的,“一向年光有限身”,這是生命的短暫和無常;“等閒離別易銷魂”,這是離別。他所寫的主題跟李后主一樣。“一向年光有限身”,“一向”是時間短暫的意思,“有限”是更短暫的意思,“有限身”也是無常的悲哀。李后主説“胭脂淚,相留醉”是離別,晏殊專門提出“等閒離別易銷魂”,兩個人的結論是不同的,即“人生長恨水長東”與“酒筵歌席莫辭頻”。在無常和離別的悲慨之中,晏殊找到一個慰藉的方法,李后主完全找不到,所以才説“胭脂淚,相留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人生總是會遭遇很多不幸,當不幸來臨時,用什麼樣的眼光去看它,用什麼樣的態度去對它?晏殊隱然有一種慰藉的辦法,所以他寫“酒筵歌席”。有聚會既可以飲酒,也可以聽歌,在這種無常離別的人生之中,你要怎麼樣來安慰自己,怎麼樣來排解、解除這種悲哀?晏殊是“酒筵歌席莫辭頻”。
杜甫的詩“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説的是“莫”。韋莊的詞“須愁春漏短,莫訴金盃滿”,用的也是“莫”字。“莫”是説你不要,本身就是一種勸解之詞。你不要推辭説酒喝得太多,“酒筵歌席莫辭頻”,“莫辭”就是不要推辭。不辭頻,不怕金盃的滿,不怕酒喝得多,“頻”是多、滿。所以晏殊是跟杜甫、韋莊一樣,隱然有一種勸解的意思。可是,晏殊跟韋莊、杜甫是不同的,韋莊最後的歸結是“凝恨對殘暉,憶君君不知”,還是回到相思懷念的悲哀。可是晏殊不是,晏殊説:“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可以知道,晏殊比他們這些人要理性,有慰藉的辦法。而他之所以得到這種慰藉辦法,是有一種理性的反省和思索在裏邊。
理性詞人與純情詞人之對比
將晏殊跟李后主做一個比較,李后主開頭的“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所寫的是眼前、當下的現象帶來了感觸,引起了我的悲哀,完全是直覺的感受。可是晏殊説“一向年光有限身”,不是一個現象,是一個概念,是經過反省思索後的結論,它們是完全不同的。也許剛聽起來覺得很奇怪,詩詞需要一種感情上的感動或觸發,怎麼會有理性呢?可晏殊恰好把他的感性和理性結合得很好。“一向年光有限身”是他的感情,他對無常的悲哀有很真實、很深刻的感受。可是,晏殊由此歸納出對於人生的了解,就是一個理性的認識。
李后主跟晏殊兩個人,形成了一個非常好的對比。同樣一種無常的感情,這兩個人反應怎樣的不同呢?李后主説,“獨自莫憑欄”,一個人的時候千萬不要靠近那個欄杆。一般樓上有欄杆,可以望遠,而望遠常常引起人的懷思。所以李后主説,不要去憑欄,尤其你獨自一人的時候。憑欄的時候看到“無限江山”,看到有山有水的故國,就是李后主的南唐故國。可是現在丟掉了那個江山,是“別時容易”,那麼容易就把它失去了,要想回去看故國的江山,是“別時容易見時難”。
李后主的結論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天上人間”四個字非常奇妙。這四個字一個“天上”,一個“人間”,沒有主語、謂語、賓語。“天上人間”是什麼意思?這可以有很多解釋。俞平伯先生在《讀詞偶得》中的解釋是,從前是天上,現在是人間,是今昔強烈的對比。他還有一個解釋,説“流水落花春去也”,春到哪去了,到天上了,還是到人間了?是問話的一種口氣。還有一種可能是“流水落花春去也”寫的是“別時容易”,“天上人間”寫的是“見時難”。其實還有一種可能,“天上人間”就是兩句哭天之詞。
總而言之,這四個字有很多種可能,詩詞可以引起多義的解釋。為什麼一句詩或者一句詞可以引起我們很多解釋?一個原因是語法的模棱。模棱,就是模棱兩可,文法不完備,就像“天上人間”,它的語法模棱兩可,可以講成感嘆或者疑問。還有一個原因是,詩詞裏邊所舉的形象可以引起人的多種聯想,如李商隱有一句詩“斷無消息石榴紅”,石榴的“紅”是什麼,可能是石榴花的紅,或是石榴裙的紅,或是石榴酒的紅,同樣的形象引起人的聯想不一樣。
李后主所説的“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水流花落,春歸去,什麼都消失了,天上人間的隔絕,是不能夠挽回的悲哀。晏殊同樣看到無限的江山,他是理性的詩人,但並不是麻木不仁,並不是沒有無常的悲慨,他的“滿目山河”是“空念遠”,這豈不是“理性的反省和思索”?因為他理性,知道不能夠馬上就到遠方去,遠方的人也不能馬上就到我這裡來,這種阻隔不是人力能夠補救和挽回的。所以,這個“空”字就跟李后主完全不同了,這是晏殊理性的反省和思索的結果。“滿目山河”是“空念遠”,“落花風雨”是不是“更傷春”?李后主寫“流水落花春去也”,他看到落花是傷春的,這是一種春天消逝的感傷,所以傷春就是“春去也”。晏殊看到花落、春去,不是麻木不仁,而是“更傷春”,這個語法呼應是有一種理性裏的感情、感情裏的理性,兩個是互相聯絡、結合在一起的。“更”是加深,第一層悲哀是離別的念遠的悲哀,再加上花落春去傷春的悲哀,所以用到“更”字。“落花風雨”是“更傷春”,“更”字是加深之詞,第二句把兩個都加重了,有念遠,更有傷春。可是他以前面的一個“空”字,可以連下來把兩個都否定,這是晏殊一個非常奇妙的地方。詩詞裏的理性思索,晏殊表現得很好。以一個“更”字把兩個同時加重,一個“空”字把兩個同時否定,上一句的“空”,跟下一句的“更”,互相結合、反襯得非常好。
晏殊將感情與理性結合得非常好,最後隱然有一個安排和解決的辦法,“不如憐取眼前人”。念遠是空的,因為這個遠人不在這裡,是白白念遠,對你是沒有好處的,一點在現實的補救都沒有,所以是“落花風雨更傷春”,這個“更傷春”同時接着上一句的“空”字下來,也是空傷春,所以現實的解決辦法是“不如憐取眼前人”。真是非常理性,你所能掌握的只有現在,念遠是你不能得到的,傷春是你不能挽留的,現在所能做的,就是“不如憐取眼前人”。“憐”是愛憐的意思。眼前的人,是能夠呼喚起你一種感情的。
韋莊的詞中有“此度見花枝,白頭誓不歸”,如果今天眼前也有花枝的話,就“不如憐取眼前人”。一定還要注意,晏殊是達觀、理性,可是同時也有感情。感情的達觀、理性之中,同時還有一個陶淵明常用的“姑且、聊且”的意思,比如“且共歡此飲”“聊為隴畝民”。陶淵明曾經也有過壯志——“撫劍獨行游”。可是他出來做官,發現官場上的腐敗黑暗,不能夠忍受,就決定“躬耕”了,但“躬耕”不是他的本意,所以他説“聊”。既然“撫劍獨行游”不可得,比較之下我就寧可、聊且、姑且做一個歸隱田園的老百姓。“且共歡此飲”,陶淵明隱居之後,有人約他一起出去做官。可是他出去做官,就是改變自己的道路,他不願改變。雖然你跟我走的道路不同,我並不願意把你看成敵人,仍然可以跟你“且共歡此飲”,姑且我們共同歡樂地在這裡一同飲酒。他説“吾駕不可回”,可是我駕車所走的道路是不能夠挽回的,你讓我走你的那條路是不行的,你不是跟我走共同道路的人,不是我真正的知己,可是沒有關係,既然相遇在一起,就共同歡樂地飲這一杯酒。所以這個“聊”跟“且”都是那種不走極端的。可是有些人是走極端的,杜甫有“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竹葉是竹葉酒,我今天如果沒有竹葉酒喝,這人間的菊花我都不教它開了,沒有這個,寧可什麼都沒有。
《浣溪沙》這首詞,是我們要證明晏殊這個理性的詞人,在感情之中表現出一種理性的思致,最好的代表作品。這首詞跟李后主做了對比,可以看到純情的詞人跟理性的詞人對於宇宙之間的現象,同樣有感情,同樣有一種感動——無常的悲哀、傷春的悲哀、離別的悲哀。可是晏殊的反應、結果跟李后主不同,這是理性的詞人跟純情的詞人的很大分別。
對大自然的敏銳
晏殊是理性的一個詞人,雖然具有理性,可仍然是一個非常敏感、銳感的詞人。他對於宇宙之間的一切現象,感受是非常敏銳的,現在我們來體會他敏感、銳感的這方面。
辛棄疾曾經寫過《踏莎行》,《踏莎行》是晚唐五代、北宋詞人常常寫的一個調子。可是辛棄疾所寫的《踏莎行》裏所表現的風格,跟晚唐五代、北宋詞人的《踏莎行》的風格完全不一樣。詞在開始的時候,所寫的大都是閨閣園亭、男女之間的相思離別,都是很溫柔、很纖細、很委曲的感情。所以辛棄疾以英雄豪傑,將詞變為豪放,不但在一些長調——本來就適合於寫豪放風格的詞裏邊表現豪放,還把晚唐五代北宋纖細委曲的婉約詞改變成豪放。
辛棄疾的《踏莎行》,跟晏殊的完全不同。晏殊所寫的,是敏感跟銳感,感覺的纖細、敘述的委曲,將那種纏綿婉轉的情意敘述得非常好。馮正中的《鵲踏枝》,寫了十幾首;溫庭筠的《菩薩蠻》也寫了十幾首。要掌握一個詞調的風格,或者要掌握一個詞人的風格,最好的辦法是把他同樣的調子一直念下去。下面來看晏殊的《踏莎行》:
第一首:
細草愁煙,幽花怯露。憑闌總是銷魂處。日高深院靜無人,時時海燕雙飛去。 帶緩羅衣,香殘蕙炷。天長不禁迢迢路。垂楊只解惹春風,何曾係得行人住。
第二首:
祖席離歌,長亭別宴。香塵已隔猶回面。居人匹馬映林嘶,行人去棹依波轉。 畫閣魂銷,高樓目斷。斜陽只送平波遠。無窮無儘是離愁,天涯地角尋思遍。
第三首:
碧海無波,瑤&有路。思量便合雙飛去。當時輕別意中人,山長水遠知何處。 綺席凝塵,香閨掩霧。紅箋小字憑誰附。高樓目盡欲黃昏,梧桐葉上蕭蕭雨。
第四首:
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樹色陰陰見。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 翠葉藏鶯,朱簾隔燕。爐香靜逐游絲轉。一場愁夢酒醒時,斜陽卻照深深院。
詞裏纏綿婉轉低回的感情,從它的聲調就可以感覺出來。晏殊是一個理性的詩人,他雖然理性,可是他的感受、感情非常纖細、非常銳敏,“小徑紅稀,芳郊綠遍”,真是寫得美!一般人寫到春歸、春去、花落,都是悲哀。杜甫曾寫道“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李后主也曾寫道“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晏殊寫的景色也是暮春的景色。
北宋周邦彥寫過一首詞:“樓上晴天碧四垂,樓前芳草接天涯。勸君莫上最高梯。 新筍已成堂下竹,落花都上燕巢泥。忍聽林表杜鵑啼。”寫的是暮春。“樓上晴天碧四垂”,樓上碧藍的天一直是垂到四垂的,因為他在高樓之上,四面一看都是地平線,都是天地相接,好像藍天一直垂到地平線上去。“樓前芳草接天涯”,綠草已經長滿了一大片。“勸君莫上最高梯”,我勸你不要登到最高樓的樓梯上去望遠,當你看到“樓上晴天碧四垂”,看到“樓前芳草接天涯”,就會有一種傷感,就會有一種傷春的心情,因為那樓前的芳草已經完全綠了,春天已經走了,夏天開始來了,初春已經過去了,這已經是暮春的景色了。所以他説“新筍已成堂下竹”,剛長出來的嫩的筍尖,已經都長成那麼高的竹子。“落花都上燕巢泥”,花不但落了,花落在塵土之中,塵土就是泥土,燕子把帶着花的泥土銜到屋樑上去做巢。春天真的走了,連落花都變成燕巢上的泥了!所以他説“忍聽林表杜鵑啼”,“忍聽”是一種“豈忍聽”的意思,怎麼能夠忍耐、忍心聽到。“林表”,樹林的外邊。杜鵑鳥是在暮春時節啼叫的鳥,它的叫聲,一般是“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你在“天涯”做客,暮春時節聽到杜鵑鳥的叫聲,你是很悲哀的,所以是“忍聽林表杜鵑啼”,而且據説杜鵑鳥的“啼”是一直“啼”到血從口中流出來。所以這個“芳草接天涯”代表的是暮春,是傷春。
周邦彥用兩句詞寫出悲哀:“勸君莫上最高梯”,“忍聽林表杜鵑啼”。晏殊的這首詞沒有明白&&他的悲哀,“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樹色陰陰見”,他寫的是一種非常纖細的、對於外界景物的感受,可是他沒有明白表現他的哀悼和傷感,而且還隱然表現了一種欣賞的意味。他所寫的,都是對於景物的感受和欣賞,晏殊對於大自然景物的變化有很敏銳的感受,詞裏表現了一種非常有詩意的、欣賞的、賞玩的感情。這是晏殊詞的另外一個特色。
晏殊的詞跟李后主的詞有很大的不同,晏殊是一個理性的詞人,他的詞裏並不是沒有感情、感受,而是有了感情、感受以後,不像李后主那樣很單純、很直接地反映,而是把打動人的感受轉化。一個理智的詞人,他能夠把所看見的很多個別的事物進化成一個觀念,比如説“一向年光有限身”就是一個概念,不是一個單純的對象,這是晏殊的一個特色。還有,理性的詞人表現得有節制、有反省,所以“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後面,接一句“不如憐取眼前人”。他不是像李后主那樣沒有節制地大段發泄,而是有節制、有反省,有一個處理的辦法。
許多讀者覺得詞所反映的都是傷春怨別、兒女情長,這個觀點是非常錯誤的。每一個詞人都有不同的特色,晏殊有非常連續、幽微、婉轉、敏銳的感受,而且是充滿了詩意的一種感受,這是大晏重要的特色,所以我們不能只看到理性,還要看到他另一方面的感情。
曲折幽微,含蓄而有節制
我們來看這首《踏莎行》。“小徑紅稀,芳郊綠遍”,“小徑紅稀”,“紅”是指什麼?是指花落。李后主所寫的是“謝了春紅”,是落花零落的生命的淒涼和凋傷的感受。晏殊所寫的落花,寫的也是“紅”,是“小徑紅稀”。我們説“林花謝了春紅”是感受,太直接,不巧妙,而這個“小徑紅稀”則是一種美感的欣賞。他不直接寫生命的凋傷,而是寫景色,裏邊可能有花落春悲的傷感,但是他不是直接寫的,而是採取了一種美感的欣賞。很多人講詩詞裏要有一種形象,這個形象在你的詩作情景中産生了作用,才是好的。比如“魚躍練川拋玉尺,鶯穿絲柳織金梭”,就沒有感動,在詩句裏不造成作用,這個形像是浪費的,所以形象如何呈現非常重要。一定要有情,而情要借景來&&。中國的文學批評中説“情景相生”,這個“情”字要看成非常廣義的“情”字,未必是喜怒悲歡這種強烈的感情。看大晏的詞,“徑”字是名詞,“紅”雖然是顏色,可他卻用這個代表花,是用一個暗指來代替一個明指的信息,他感覺很敏銳,而且寫得非常婉轉。《浣溪沙》中“小園香徑獨徘徊”,他在開滿了花的小徑之中,一個人在那裏徘徊。這個“小”字,訴盡了他的這種感受,一種小徑曲折、幽微,花落以後的很敏銳的感受。
“芳郊綠遍”,芳郊是長滿了芳草的郊野,到處是芳草,“綠遍”天涯。“綠遍”,一片青青的綠色。中國詩詞裏有一種傳統,在用到某一些詞和句子的時候,能喚起民族意識裏千百年來所留存的某種共同的反應。北大教授林庚曾經寫過一篇論文,專門談論唐詩的語言問題。中國一説到芳草,常有懷人的意味。漢朝樂府詩《飲馬長城窟行》第一句就是“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可以看到那綠遍天涯的芳草,“綿綿”不斷絕的樣子。《楚辭》裏也有“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王維有一首送別的詩裏曾經寫過“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六朝時江淹寫過一篇《別賦》,開頭兩句是“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斷腸芳草地”,使我斷腸的是那個芳草的一片綠顏色。
芳草可以給人這麼多感情上的感受,可是晏殊與他們不一樣,他沒有用很強烈、生硬的句子,只是“芳郊綠遍”,只是表面上寫一個景色,是“小徑”的“紅稀”,“芳郊”的“綠遍”,在“小徑紅稀”之中,“芳郊綠遍”之中,你是什麼樣的感受?大晏很微妙的一點是他寫得很閒適,寫得很小心,他注意到紅的慢慢稀少,花園裏的花開始零落。
寫花慢慢地落下來,秦少游有一首詞的開頭是“梅英疏淡,冰澌溶泄,東風暗換年華”。“英”是花的花瓣,“梅英疏淡”,梅花的花瓣,“疏”是晏殊所寫的“稀”,稀少的“稀”,“梅英”的“疏”,就是稀少的意思。“淡”是它的顏色變淺了。花含苞的時候顏色比較紅,等它慢慢綻開的時候,顏色就比較淺了。梅花的花瓣,從多到少,花瓣的顏色,從深到淺。“冰澌溶泄”,水上的冰慢慢地薄了、融化了,慢慢順着水流走了,一步一步地進行,就是“東風暗換年華”。東風在暗中,把這一年的芳華看淡了,詩人對景色有敏銳的感覺。所以晏殊的“小徑紅稀,芳郊綠遍”,不僅是寫景色的美,還寫感受的細緻,看到那個情景小小的變化,一步一步地進行,從“小徑紅稀”到“芳郊綠遍”,然後是“高&樹色陰陰見”,花落了,草綠了,樹蔭就鋪滿了一片。
唐朝詩人杜牧有一首很有名的七言絕句,“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有人説杜牧年輕時鍾情一個女孩子,本答應過幾年回來迎娶,卻因為做官失言,再次相見對方已結婚生子,所以就寫了這麼一首詩。當年很新鮮的花朵,現在已經被狂風完全地吹落,長了滿樹的綠葉。很多花開花的時候不長葉,等到花落了,葉子才長出來。這個綠葉成陰是“狂風落盡深紅色”後的第二步,花落以後才長出葉子,等到綠葉成陰,就花落很久了。杜牧的這兩句詩寫得比較明白,可是大晏的詞沒有明白寫出來狂風吹盡,沒有明白寫出來光陰的消逝,他只是寫景色,“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樹色陰陰見。”“高&”,你站在一個高&上,“陰陰”就是濃密的樣子,“見”是突然看到高&上樹木的濃陰一天比一天密,春天一天比一天消逝得遠。這三句他表面上寫的景物,沒有像剛才所舉的詩人詞人抒寫感情。
下面寫道“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等到花落春歸、綠葉成陰的時候,“春風不解禁楊花”。“楊花”就是柳絮,在春天的時候,有很大片的柳絮。一棵柳樹在春天來臨時,柳條是慢慢地變成嫩黃、嫩綠,慢慢地長出葉子。這句話很寫真的一點就是,當柳枝變綠的時候,就開始有楊花,楊花飛起來的時候,就是滿天飛舞,非常濃密。《紅樓夢》裏,林黛玉跟薛寶釵她們聚會的時候填詞,就是填的柳絮詞,“粉墮百花洲,香殘燕子樓,一團團逐對成球”。“粉墮百花洲”,柳絮飛得好像是百花洲上的花飄落了,粉代表花。“香殘燕子樓”,是説燕子樓上住的那位女孩子死了,美麗的柳絮的飛舞,像是花落、像是美人的死亡。“一團團逐對成球”,這樣逐對逐對一團團的,“成球”就是滾成球的樣子。北京有很多柳樹,春天當你走過的時候,很多柳絮飛舞,就像晏殊寫的,北方暮春時節,滿天飛舞的柳絮,“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柳絮是非常輕飄的,迷迷濛濛的,所以是“濛濛亂撲行人面”。
這首詞整個上半闋,晏殊沒有寫一個透露感情的字眼,而是用形容詞寫情景的轉變。他沒有説傷春、懷人,只是寫景物,寫得那麼含蓄。他是把讀者帶入景色之中去感受,不是讓“我”説出來:“我”在傷春,“我”在懷人。當你走在春天的小徑上,柳絮濛濛的一片,撲到你的臉上,當你看到“小徑紅稀,芳郊綠遍。高&樹色陰陰見”,當你看到滿天柳絮飛舞,飛到你的眼前,你是什麼感受?他只用三個字稍微透露了一點點感情,“春風不解禁楊花”,所有的表現情緒的字句都在“不解禁”三個字裏。“不解禁”,就是不知道阻止。春風,你為什麼不知道阻止楊花,竟然就讓楊花這麼迷蒙的一片,直撲到我們行人臉上來,你為什麼把這種零落、飄零,暮春的悲哀、淒涼,徑直打到我的臉上來,“濛濛亂撲行人面”。他的感受都很直接地説出來,用詩人的敏銳、詩意、纖細,把所感受到的那種細膩幽微帶到你的眼前、心底,讓你去親自感受。
這首詞上半闕是以外面的景色為主,晏殊之所以寫得不雜亂,因為他在寫外面景色的時候,有一種時間消逝的感覺,他是在行進之中,從“小徑紅稀,芳郊綠遍”到“高&樹色陰陰見”,到“春風不解禁楊花,濛濛亂撲行人面”,春天一天比一天消逝,它的結構是時間的消逝。這首詞下半闕有一個大的轉變,是由外而內,“翠葉藏鶯,朱簾隔燕”,他還是寫得很細膩,春天的時候有黃鶯鳥,只聽到黃鶯鳥的叫聲,可是看不到,所以説“翠葉藏鶯”。“翠葉藏鶯”當然是接着前面的景色來寫的。我們來分析這首詞的結構,前面都是景色,一直到上半闋的最後一句,有人出來了,是“濛濛亂撲行人面”。接下來“翠葉藏鶯”,“鶯”是藏在陰陰的樹色裏,而你知道有鶯,因為聽見了鶯啼。暮春的時候,黃鶯鳥的叫聲人能聽見。後面“朱簾隔燕”,這是寫得很妙的一句詞,好處有幾點,一個是結構上的,“燕”是燕子,是屬於大自然的,可“朱簾”是房子,所以從外邊轉到裏邊來。“朱簾隔燕”,人在簾內看到朱簾外的燕子在飛,從外而內,從景到人。不只如此,晏殊沒有把這首詞的整個情調破壞,還是都用形容詞來寫。“隔”字雖然是動詞,可是它所呈現的是一種景象,是説燕子在簾外飛,所以還是從景象來寫的。
“翠葉藏鶯,朱簾隔燕”,他寫的是房間裏的人,房間外的景色。“爐香靜逐游絲轉”,寫得很美麗。宋朝最講究燃香,南宋詞人王沂孫有一首詞,詞調名叫做《天香》,咏一個龍涎香。龍涎香是宋朝人常常點的香,是一種很有特色的香,製造、燃燒都有固定的方法。龍涎香最大的特色是它的香煙,是碧綠的,而且凝聚不散,一直在那裏盤旋裊動,是凝聚而不散的香氣。晏殊的這首詞雖然不是正式寫香,可是宋朝當時的社會風氣是講究燃香的,所以他説“爐香靜逐游絲轉”,“轉”是香煙繚繞,一縷香氣在盤旋繚繞,凝聚不散。香爐裏的煙是“靜逐游絲轉”。什麼是游絲呢?春天當花樹生長的時候,有一些細小的昆蟲,也在春天生長,這些昆蟲有一種分泌物,吐出來的絲是長長的一條絲,可以看到天上飄着一條很長的絲,卻不知道是哪來的,這個叫做游絲。如果春天天氣暖和了,把窗跟門打開,柳絮游絲可以飄到屋裏來,晏殊寫的是這種情景。外邊空中的游絲,屋裏邊爐煙的香氣,就是“爐香靜逐游絲轉”。
最後就是在這樣外在的景象跟內在的景象之中,“一場愁夢酒醒時”。他曾經飲酒而醉臥,夢是“愁夢”,是夢中所追尋的沒有得到。“斜陽卻照深深院”,到下午的時候,太陽已經西斜,斜陽照在深深的院落之中。大晏詞不像杜甫的詩有那麼博大的感情,表達忠君愛國、關懷國計民生的理想。可是他寫出了非常纖細、幽微、婉轉的一種詩人的感受,這是大晏詞的另外一個特色。
大晏寫感情不是很放縱,不是寫得很強烈、激昂慷慨,他寫得很含蓄、很有節制,可是有一首詞他寫得激昂慷慨的,就是《山亭柳》。這首詞的風格,在晏殊的詞裏邊是比較特殊的一首。每個作者都有獨特的風格,如同天下沒有兩個完全相似的人一樣,詩跟詞等文學作品也不應該有完全相同的風格,無論是溫、韋、馮、李,還是大晏,我們所説的特色,不是説他作品裏有一首詞或者兩首詞是這樣。這個風格不但足以代表他作品的風格,而且足以代表他自己做人的風格,是個人跟作品合一的一種最能夠代表他的特色。可是有的時候,他的作品裏有偶然的例外,跟他一般風格不相同的情形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