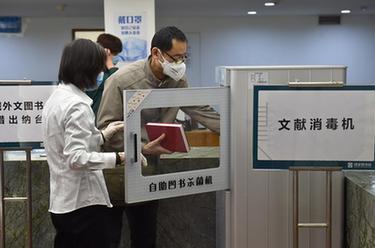5月10日永定河來水。石秀英攝
永定河,“活”了。
經歷數十年大部分河道乾涸後,這條源自山西、流經河北、哺育北京、匯入天津的河流,5月12日水頭已漫過北京與河北交界處,很快即可重見全線通水。
河道裏水頭奔涌、河岸上人頭攢動,大量視頻在一個個手機屏上閃爍——原來永定河真的是一條河。
人們已許久沒看到永定河舞動的身影了,這身影裏曾蘊含慈愛,曾顯露暴怒,無數悲歡、複雜況味、諸般記憶本已風乾在裸露的河床上,隨著水流復起,依稀浮現。
不過,這次水流並非永定河自身來水,主要是從流域外引來的客水。引客水的目的是為了讓永定河真正“活”過來,恢復全流域生態系統,常年不斷流。為實現這一目標,沿岸已付出許多努力,還在用心爭取。
土肥原係黃沙過
從遠古流來的永定河,和人類親密接觸後有過13個名字,小黃河是永定河的曾用名之一。
這次來水引自黃河。通過萬家寨引黃工程調引黃河水,從3月15日開始,山西冊田水庫開閘放水,將生態水源源不斷地匯入到永定河上遊。
説來永定河與黃河頗有淵源。
永定河上遊為桑幹河,在河北與洋河交匯後稱永定河。發源於山西寧武縣管涔山北麓,舊志稱其發源於管涔山天池,不準確,天池在管涔山南麓,屬汾河發源地區域,將桑幹河和汾河發源地隔開的山叫分水嶺,傳説兩河發源地隔山潛通。
據唐代《元和郡縣誌》記載,北魏孝文帝曾在天池做過實驗,“以金珠穿魚七頭,放此池,後於桑幹源得之。猶為不信。復以金縷拖羊箭,射大魚。久之,又于桑幹水得所射箭。乃知潛通之説不虛矣。”
明廖希顏《三關志》稱:有人乘車過天池,車被風刮到水裏,後來在桑幹源找到了車輪。清人曾有詩云:“天池飄墜車輪在,金珠又見七魚穿。&&潛沒真奇絕,混混日夜崑崙泄。”
汾河是黃河第二大支流,永定河與黃河的淵源還不止於此。永定河主要支流洋河發源於內蒙古,近現代多名中外學者認為,古黃河在河套平原向東接洋河,之後由於地殼變動才轉向南,也就是説洋河本為古黃河故道,
有關永定河的文獻記載可以上溯2500多年,永定河形成則是幾百萬年以前的事了。在漫長的歲月裏,和黃河一樣,永定河也從黃土高原攜帶泥沙涌向下游,久而久之,形成洪積、沖積扇,河流不斷改道,洪積沖積扇逐漸發育,慢慢地連為一體,成為平原,地質學上稱北京平原。
20世紀初,美國地質學者維裏士(Bailey Willis)來到北京,他考察了這個“C形”環山的名城,寫道:“中國的東部,自北緯40度起,有大平原向北入叢山,形如海灣……從平原以視,其四圍之山嶺,猶海灣之於石壁。”他將之稱為“北京灣”。
葉良輔先生在《北京西山地質志》中引述了維裏士的見解,認為把北京平原命名為北京灣,“似乎正當。此言可想見平原之形狀也”,並進一步研究認為“北京灣乃為河流氾濫之平原矣”。
這條河流是永定河,北京的母親河。
永定河之名為1698年康熙皇帝所賜。康熙為永定河花了不少心思,也常在河上流連吟咏。比如這首《舟中觀耕種》:“四野春耕阡陌安,徐牽密纜望河干。土肥原係黃沙過,辛苦先年挽異瀾。”第三句是説永定河氾濫帶來黃沙淤積,治河之后土壤肥沃適於耕種。
這句詩也道出了永定河與北京最深層的&&,永定河沖積形成平原,為人們提供了可生息繁衍的土地。
先民們在這片土地上狩獵耕耘,聚落在永定河邊慢慢擴大。
去年12月30日京張高鐵開通,但想坐高鐵從石家莊到張家口,要先到北京西站再轉北京北站(或清河站),無形中增加了在北京的停留時間。這一情況可以説古已有之。
北京一帶是自然形成的交通樞紐,太行山東麓大道(今京港澳高速方向)、居庸關大道(今京藏高速方向)、古北口大道(今大廣高速北段方向)、山海關大道(今京哈高速方向)交匯於此。而永定河橫亙其中,行人至此,難免盤桓。渡口交通需求使聚落規模擴大、功能增強。
先民們選擇距永定河渡口不遠,又能回避洪水侵擾,還可保證水源供應的所在居住,這就是薊丘。它是永定河渡口東北方約10公里的一處高地,生長著多刺的野生植物大薊。後來,人越聚越多,形成城市,稱為薊。
《禮記·樂記》載:“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説的是周武王滅商後將黃帝的後人(《史記》稱是帝堯的後人)封在薊。薊在今北京廣安門一帶,薊丘在白雲觀附近。
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先生認為,薊的原始聚落“到正式建立為諸侯國的時候,就完全具備了城市的功能,因此也就可以認為是建城的開始”。而今,在廣安門南護河西岸有個紀念碑,碑頂上書:“北京城區,肇始斯地,其時惟周,其名曰薊。”
薊形成城市功能,與永定河密不可分。之後,戰國燕都、遼南京城、金中都城都是在薊城的基礎上發展的。城市能夠發展,水源舉足輕重。據《水經注》記述,永定河古代在北京一帶多次改道或分汊漫流,為城市提供了豐沛水源。
這次永定河來水,水頭在乾涸的河床上自由流淌,倒有一絲古永定河遺風。遠古以來,永定河道在北京灣裏來回擺動,如今北京城內河流、湖沼大都是永定河故道遺存,如涼水河、龍河、鳳河、天堂河、蓮花池、積水潭、北海、中海,等等。比如薊城西北原有個大湖,也稱西湖,為眾多泉水匯聚,曾是永定河的潴水湖,是薊城主要水源,遺跡為今蓮花池。
蓮花池本已乾涸,1981年設計北京西站時原本擬佔用,侯仁之先生力主保護,最終西站建設增加了14億拆遷費,位置向東北方向移動100多米,留住了蓮花池舊址,還設法保留了一個水面,算是對這個最早滋養北京城的地面水源進行紀念。
永定河水給人們帶來的也不光是滋養。
傷心最是桑幹水
永定河曾用名還有浴水、&水、桑幹河、高梁河、渾河、盧溝河、無定河等。其名無定,是因為泥沙含量大,淤積嚴重,河道不定。
歷史上,水災是北京一帶危害最大的自然災害,其中永定河氾濫造成的災害最嚴重。
永定河從高原流下,于河北懷來官廳村附近衝進重重山脈,在山巒中奔涌100多公里,海拔連續下降,水勢不斷增強,到北京門頭溝三家店出山。水量大時,落差加上峽谷效應,水流湍急,在一望無際的平原上形成難以抵擋的力量。
從史料中統計北京水災顯示:元代97年,發生水災年份52個;明代276年,發生水災年份116個;清代267年,發生水災年份達129個,其中特大水災5次,永定河佔4次。
康熙七年(1668年)七月,連日大雨,衝開永定河大堤,水流涌進京城。據記載:“(洪水)直入正陽、崇文、宣武、齊化諸門。午門浸崩一角。五城以水災壓死人數上聞,北隅已民亡一百四十余人。上(康熙)登午門觀水勢……”
如同一部“災難大片”。時人彭孫貽著《客舍偶聞》中記述:宣武門一帶水深五尺,洪水漫過城壕,淹沒橋梁,水聲如雷,水勢似瀉。有賣菜者,被激流衝過城門,人和貨擔轉眼無蹤。有騎駱駝者,被衝進禦河,人抱樹得免,駱駝淹死。宣武、朝陽等城門一帶,城外淹死者的屍體漂流進城。路上水大不便騎馬,漢族官員多坐肩抬的小轎,滿族官員按例不能乘輿,就找人牽馬而行,官員坐在馬背上蹺著腳以免濕鞋,有個侍郎太胖蹺腳困難,找了個大澡盆用人推著上朝。盧溝橋以下良鄉、涿州、霸州都被洪水淹沒,經過20多天才退去。
觸目驚心,康熙把治河和平定三藩、漕運一起列為親政後的頭等大事,命人刻在大殿廊柱上,時時警示。
在全國大的戰事基本平息之後,從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起直到他去世,30年的時間裏,康熙親自主持對永定河中下游進行了多次治理,較大的工程有7次,尤以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的治理最有效。
那年二三月間永定河自新城九花&漫決,霸州受災。康熙到災區看到,田畝淹泡,民多失所,以水藻為食,生計困難。深為憐憫,令直隸巡撫于成龍(字振甲)勘察詳情,決定以挑河築堤的方式進行治理,工程浩大,共佔民地139頃62畝,用銀3萬兩,挑河145里,南岸築堤82里,北岸築堤102里。到7月21日,工程完工。于成龍上書康熙:“乞賜河名,並敇建河神廟。”康熙下旨:“照該撫所請,賜名永定河,建廟立碑。”
康熙禦制碑文,稱“念茲永定河,其初也無定。蓋緣河所從來遠……夾山而下。至都城南,土疏衝激,數徙善潰,頗壞田廬,為吾民所苦。朕甚憫之……”文中記述治河情況後,賜名還封了河神。“名曰永定,封為河神。”
康熙敇建的永定河神廟址在盧溝橋旁,今已無存。他兒子雍正也建了一個河神廟,在今首鋼制氧廠西南角,尚存碑亭,內有雍正禦制碑文,其中稱永定河的敇封從康熙開始,不確切。
正史記載,永定河獲得的第一個冊封是安平侯。《金史·禮志》載:“有司言,盧溝河水勢泛決,嚙民田,乞官為封冊神號。禮官以祀典所不載,難之。已而,特封安平侯,建廟。”
看來這次冊封還有點曲折,《大金集禮》中説得詳細些,大致情況是,1179年,有人提議永定河造成災害,要冊封它(類似招安),但管事的比較認真,提出冊封應該是五嶽那樣的名山,永定河這樣的“山林川澤”之神,有功德才能封,因造成災害而封,不合適,金世宗就沒有冊封。1185年,永定河又發了大水,皇帝組織抗洪失敗。1187年,冊封下來了。
管事的太死板,都城建在河邊,永定河就不是一般的“山林川澤”之神了。到了元代,忽必烈又兩次冊封,河神由侯晉陞為公,稱顯應洪濟公。
忽必烈所封是桑幹河神。從隋唐到元明,永定河不止一個名字,但桑幹河(或桑幹水)之名一直是對永定河上下游的統稱。永定河從雁北地區流到渤海附近,全長700多公里,這一區域地處遊牧與農耕文明交匯地帶,除了水災,它還以桑幹河之名留下許多人文記憶。
唐劉皂《渡桑幹》“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又渡桑幹水,卻望并州是故鄉。”宋蘇轍《渡桑幹》:“會同&&凡十日,腥膻酸薄不可食。羊脩乳粥差便人,風隧沙場不宜客。”唐宋時期,桑幹河是邊遠之地,渡桑幹總是讓遠行客心旌搖曳、感觸良多。
《全唐詩》中,含有桑幹之名的作品頗有一些,多與戰事有關。駱賓王“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王昌齡“將軍降匈奴,國使沒桑乾。”李白“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蔥河道。”
“傷心最是桑幹水,血濺流澌去未涯。”這句詩的作者是明代沈煉。電影《繡春刀》中主人公是明代錦衣衛沈煉,歷史上這個沈煉也有錦衣衛經歷,但他不是武林高手,是以死抗爭權姦嚴嵩的一代名臣。他被貶居桑幹河畔的河北懷來,後在那裏遇害。
休教東入紫荊關
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及北京市延慶區)是官廳水庫的所在地。這個新中國建設的第一座水庫改變了永定河。
康熙賜名“永定”,在治河上也確實很用心,挑河築堤工程完成後,次年夏連降大雨,堤防有坍卸,他深感不安,10月親往勘察,在郭家務村南大堤上,自己用水平測量儀在冰上測驗,發現問題告訴官員:“此處河內淤墊,較堤外略高,是以冰凍直至堤邊。以此觀之,下流出口之處,其淤高必甚於此。”要求春水發前進行疏通加固,並提醒加固河堤時不能從近處取土,“若取土成溝,水流溝內,有傷堤根”。
永定河在康熙執政後期不再“無定”。《畿輔通志》稱:“湍水軌道橫流,以寧三十年來河無遷徙,此古所未有也。”並非過譽,但這河也沒能“永定”,1912年到1949年,北京發生了6次大水災,全部與永定河有關。
1939年7月北京地區連降暴雨,永定河在盧溝橋以下多處決口,洪水在良鄉、房山、大興氾濫成災,僅良鄉、大興就有5萬戶受災,2萬戶傾家蕩産,京漢、京津鐵路被衝斷。8月31日《大公報》載:“自北平南郊至保定,茫茫無邊際。”9月2日《申報》稱:“無家可歸者已達數百萬。”10月18日《字林西報》報道:“(津浦)鐵路以西鄉野,極目所見者類似大湖沼,偶有地面村落較高之房屋,猶在水中,若海中島嶼然。秋季之穀類,以及日方期望至高之著名棉花,均已全毀……秋收全告絕望……糧食斷絕……則地面積水,未必能在明年夏季降水之前退盡,故另一季收成亦將無望,而災荒至少將歷兩載也。”
1949年11月,新中國成立剛一個多月,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在全國解放區水利聯席會議上,審議了永定河流域整治開發計劃,決定立即報請中央盡快考慮治理永定河和修建官廳水庫。次年,周恩來總理主持批准修建永定河上遊的官廳水庫,以控制永定河的洪水,並作為首都水源。
1950年8月24日,周恩來在中華全國自然科學工作者代表會議上説:“華北的永定河,實際上是無定的,清朝的皇帝封它為‘永定’,它還是時常氾濫。不去治它,只是封它,有什麼用?”
1951年10月,官廳水庫破土動工。
在永定河上遊官廳山峽建築水壩治水,不是當代人的創意。
乾隆六年(1741年),直隸河道總督高斌提出上攔、中泄、下排的永定河治理方案。上攔就是在永定河上遊“就近取石,堆疊玲瓏之壩,以勒其洶暴之勢,則下游之患,可以稍減”,並主張“層層截頓,以殺其勢”。第一次將永定河的治理思路引向上遊,高斌的建議得到實施,在懷來等地建了三處玲瓏壩,但堆砌的石壩後被沖毀,沒有發揮多少作用。
同治十二年(1873年),懷安知縣鄒振岳給永定河道上書《上遊置壩節宣水勢稟》,指出永定河水患主要在於上游水太驟,下游不能容,再次提出在官廳山峽築壩的建議,並指出高斌築壩失敗主要是因為是亂石堆砌,應建築整齊堅固的大壩。永定河道組織實地調查,認為花費太大、涉及問題多,否決了這一建議。之後左宗棠負責永定河治理時,倒認可鄒振岳的想法,不過限于當時的條件,沒能有效實施。
官廳水庫工程是當時舉國矚目的重大水利工程,得到了全國各地的支援。庫區111個村,5.2萬多人服從建設需要,分散到張北、尚義、涿鹿、懷安等8個縣。其中張北、尚義屬壩上地區,高寒貧瘠,自然條件與懷來相差甚遠,但移民都很快進行了搬遷。近年在壩上採訪,還常遇到當年官廳水庫的移民家庭。
1953年汛期前,官廳水庫大壩建成蓄水。這年8月份,永定河上遊發生洪水,洪峰流量達每秒3700立方米,水庫攔洪後下泄流量減少到每秒800立方米。高斌提出的上遊攔阻以解決永定河水災的設想,212年後,得以實現。
1954年4月,毛澤東主席到官廳水庫工地視察。1954年5月13日,官廳水庫舉行竣工慶祝大會,水利部部長傅作義講話。他説,官廳水庫的落成是把水害變成水利的重要工程,是改變自然面貌的不朽事業,全國人民都會記得和感激這件事情的。講話後,他把毛澤東主席親筆題詞“慶祝官廳水庫工程勝利完成”的金線刺繡錦旗授予水庫的建設者們。
官廳本是村名,現在是一個鎮,據傳明代在此設有“把水官”監視水情,故名官廳。1958年秋,葉劍英元帥到水庫參觀,即興題詩:“兇洪制服堤千尺,發電功能水一輪。永定河今真永定,官廳不靠靠人民。”
在這一年,桑幹河上開始建設冊田水庫,上遊層層攔蓄的格局逐漸形成。之後,隨著社會發展,用水量增大,永定河下游水量逐漸減少,直至乾涸。
5月12日,從冊田水庫放出,流經官廳水庫等的永定河水流出北京,進入河北固安。這表明170公里的永定河北京段25年來第一次全線通水。這一天不少固安人趕到河邊看水、拍攝、發朋友圈。
500多年前,固安人蘇志皋任山西按察使,曾在桑幹河邊作詩云:“吾鄉最苦桑幹水,今日尋源到此間。説與山靈牢記取,休教東入紫荊關。”
青山綠水萬家鄰
盧溝橋名字來自盧溝河,盧在這裡是黑的意思,盧溝河是説河流渾濁不清,而永定河還有一個曾用名——清泉河。
清泉河之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使用,盧溝河之名出現在金代以後。河名更替,反映著永定河環境嬗變。
遼金之前,永定河流域森林茂密,生態環境較好。從宋遼繪製的一些地圖中,還可以看到永定河流域的森林分佈,如《晉獻契丹全燕之圖》中,在今延慶、懷來、宣化北部繪著茂密森林,註明“松林廣數千里”。
從遼金開始,北京地位不停提升,城市規模不斷擴大,基礎建設和社會生活對木材和土地的需求相應增加。美輪美奐的建築興起,成方連片的林草衰減。《大金國志》記載:金太宗天會十三年(1135年)曾組織40萬人到蔚州伐木。元大都建築宏偉,當時有民諺稱“大都出,西山兀”。明清北京周邊山林都有專門的伐木燒炭機構,清代西山煤炭開採也破壞了植被。
目前所見,永定河水災的最早記載,是西晉元康五年(295年)。但遼金以前,水災的記載總體上不多,遼金以後永定河水災的記載增加,説明流域森林砍伐過多,水土流失加劇,河水攜帶泥沙量提升,淤積速度加快。
為建城傷了河,河反過來也要傷城。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所説:“我們不要過分陶醉於我們對自然界的勝利,對於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每一次勝利,在第一步都確實取得了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卻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第一個結果又取消了。”
恩格斯舉的例子有美索不達米亞、希臘等地人們為增加耕地砍森林,結果沒了森林也失去了貯存水分的中心,最後成了荒蕪之地,與永定河的情況有些類似。恩格斯説:“我們對自然界的整個統治,是在於我們比其他一切動物強,能夠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這在永定河的實踐中也有了體現。
官廳水庫建成後,從1958年開始永定河基本沒發生過大的水災,且為北京城的供水供電提供了充足的保障。但20世紀70年代後永定河上游來水不斷減少,三家店以下常年斷流,乾涸的河床成了風沙源。20世紀90年代後,污水和廢棄物增加,官廳水庫水體污染加重,1997年退出北京飲用水供水系統。
永定河源頭在管涔山北麓朔州市神頭泉,這個泉最大流量曾達到每秒9.28立方米,上世紀60年代後開始不斷衰減,到2013年的流量降低到每秒3.69立方米。當地管理部門介紹説,人為因素是造成水量減少的最主要原因。如植被破壞,水開採量過大,採煤時的排水漏水等。
儘管如此,源頭附近的桑幹河,河水寬六七米左右,是記者沿桑幹河——永定河行走所見原生狀態最好的一段河流。從源頭下行60公里到應縣,雖未出朔州市,但桑幹河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開始斷流,農民澆地要從上游水庫買水。再走100多公里到河北境內,前些年乾涸情況更為嚴重。
拯救永定河行動早已開始,國家制定了《21世紀初期首都水資源可持續利用規劃》,在上遊河北、山西等地開展工農業生産結構調整、水土保持等工作。到2003年,河北張家口、承德兩市年減少廢水污水排放800多萬噸,蓄水保水200多萬立方米。
從2003年開始,水利部協調河北、山西兩省連續6年向北京集中輸水,累計輸水3.1億立方米。與此同時,河北、山西關停了永定河上遊一批污染企業。北京市在官廳水庫三個入口處建設了濕地。2007年,官廳水庫恢復為北京飲用水源地。
2016年,國家發改委、水利部、國家林業局聯合製定《永定河綜合治理與生態修復總體方案》,提出用5至10年時間,逐步恢復永定河生態系統,將永定河打造為貫穿京津冀晉的綠色生態廊道。
2017年,永定河綜合治理與生態修復全面實施,6月,首次從黃河向永定河進行生態補水,桑幹河山西段實現了全線通水。
2018年,永定河流域投資有限公司組建成立,建立了政府與市場兩手發力的流域綜合治理新機制。
2019年,永定河生態補水3.45億立方米,300天以上不斷流的通水河段達到513公里。
今春,永定河引黃水量和補水規模為歷年同期之最。
為保證生態補水的順利,沿岸進行了不少努力。如朔州市對可能影響正常補水的情況進行排查整治,對沿河主要引水、提水的設施和險情險段實行專人專管,防止跑水、漏水。流域生態恢復的努力也在緊張進行。
生態補水使永定河沿線河道周邊地下水位整體上有不同幅度回升,北京山峽段地下水位上升明顯,門頭溝區部分泉眼停噴30年後已開始復涌。
永定河北京段全線通水後,三家店以下形成水面面積2100公頃,和補水前相比,永定河門頭溝至大興西麻各莊沿線地下水埋深平均回升2.07米。
“青山綠水萬家鄰,一井川原畫障新。紫塞風光推獨擅,錦城佳麗入橫陳。”元人李溥光這首《漯陽道中》描繪的是永定河沿岸的風光,這裡也曾秀美宜人。只要用心努力,有望將水流留下來,將永定河留下來。(記者王文化)

-
大數據"坑熟客",技術之罪需規則規避
2018-03-02 08:58:39
-
高質量發展,怎麼消除“游離感”?
2018-03-02 08:58:39
-
學校只剩一名學生,她卻堅守了18年
2018-03-01 14:40:53
-
有重大變動!騎共享單車的一定要注意了
2018-03-01 14:40:53
-
2018年,樓市會有哪些新變化?
2018-03-01 0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