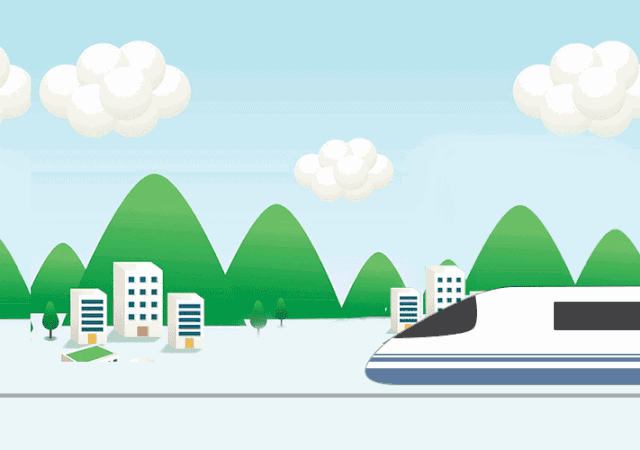問渠哪得清如許?勿忘湖北“小河南”
為南水北調源頭丹江口水庫建設跨省搬遷的大柴湖移民往事

移民們靠著肩扛車拉改造大柴湖。湖北大柴湖教育基地提供

丹江口水庫河南淅川移民安置到湖北示意圖。制圖:閆天雷

乘船下湖北大柴湖的河南淅川移民。湖北大柴湖教育基地提供
有一年清明,楊俊道領著全家從湖北大柴湖回河南淅川掃墓。那時孫子楊凱還小,楊俊道指著水庫對楊凱説,“咱們家以前住的地方就在水裏面,為了建丹江口水庫搬走了,咱們的貢獻是不是很大?”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楊俊道激動地對已經在北京工作的楊凱説,“我吃的是丹江水,你吃的也是丹江水。”
上世紀60年代,4.9萬淅川移民集中搬遷到柴湖,這裏也成為全國最大的移民集中安置區。半個世紀過去,這裏一直説著河南話、唱的豫劇、吃的麵條、喝的胡辣湯,日子還是按著老家河南淅川的規矩。柴湖也因此被稱為湖北的“小河南”
“一條扁擔兩個筐,收拾收拾下鐘祥”
全坑村的臨時碼頭是亂得不能再亂了。當時18歲的全淅林只記得到處都是人,幾乎所有人都在哭,只有第一次坐船的小孩高興。
人們要麼坐在卡車上探出身哭著道別,要麼在押送家具的船上抹著淚朝岸上揮手。誰也沒時間注意墻壁上刷的“為革命搬遷”標語。1968年初,移民搬遷工作隊進了村,村裏的空墻都刷上了這條標語。當時這裏還是一片空地,後來水漲上來,成了臨時碼頭。
全坑村隸屬于河南淅川縣,當時差兩天就是端午節。母親坐卡車走陸路,全淅林押著刷有自己名字的床板和一口箱子走水路。船上是家家戶戶的家當,石磨、犁耙、水缸、桌椅、箱櫃、耕牛,甚至是老壽木......摞得滿滿一船。一些人臨上車前還刨了半袋黃土帶上,一些人甚至挖走了一塊自家院子裏鋪的青石板。
“一條扁擔兩個筐,收拾收拾下鐘祥。”全淅林回憶,其實沒什麼值錢的家當,移民們把能帶走的幾乎都拆了裝上船。
兩年前,為了建設丹江口大壩,已經有一萬多名住在海拔130米以下的淅川移民,分兩批南下去了湖北鐘祥縣柴湖。柴湖通稱“大柴湖”。現在輪到海拔147米以下的第三批移民了,共三萬多人。
1953年2月19日,毛澤東視察長江,提出“南方水多,北方水少,能不能把南方的水借給北方一些?”他用手中的鉛筆在地圖上久久地指著丹江口一帶。在這次視察中,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南水北調”的設想。五年後,在成都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興建丹江口水利樞紐工程的提議被批準。當年9月,丹江口水庫動工。
1967年丹江口大壩下閘蓄水。淅川縣是丹江口水庫重點淹沒區。從1966年到1968年,河南、湖北兩省共搬遷38萬人,淅川縣的移民佔了20萬人。遷往湖北的淅川移民有7.5萬,其中,2.6萬人分散安置在當時的荊門縣,4.9萬人集中安置在當時的鐘祥縣大柴湖。
有一些人任憑移民搬遷工作隊怎麼勸都不走,寧願在岸邊搭個草棚住。
原來,早在丹江口水庫建設初期,淅川就有一批兩萬多人的庫區移民遷至青海,但適應不了海拔3000多米的高原。好不容易得以返遷的移民,還未站穩腳跟,又聽到搬遷大柴湖的動員通知。
“哪裏黃土不埋人,你不走等著喂魚啊!”眼看著水沒過了莊稼地、漫到了門檻,漲到了搭的草棚,“釘子戶”們也不得不踏上搬遷的船。
船在丹江裏走了一夜,轉陸路到襄樊之後,再走漢江水路。在路上的時候,淅川縣雙河村的移民穆文奇不由得開始想像今後的生活。他想既然叫大柴湖,必定是好地方,“柴就是柴火,湖就有大米”。雙河村缺柴,要燒柴必須走上40裏路到深山去才砍得到。大米在雙河也是稀罕物,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舍得用兩斤玉米換來一斤大米,“嘗個新鮮,當肉吃”。
三天之後,移民們從鐘祥大同碼頭上了岸。 兩米多高的蘆葦遮天蔽日,到處都是水窩子。從碼頭越往裏走越荒涼,腳下沒有路,沒走幾步接待的車就陷進沼澤地裏了,喘著粗氣,車輪濺起的泥漿把推車的移民潑成了泥人。
咬牙扛下來的移民安置任務
全淅林跟著移民們跳下汽車,一腳深一腳淺地蹚著污水,硬著頭皮鑽進蘆葦林,在當地移民接待站幹部的引導下找到了自己的屋子。為了方便管理,移民還是按照在淅川的大隊隊別居住,大隊稱謂和幹部都沒變。
移民安置房就建在剛剛砍過的蘆葦地裏,十間一排,矮矮的,就像部隊的營房。全淅林一看,這房子除了四根柱子是磚壘的,其他墻都只是蘆葦稈糊上泥巴。
政策規定,每個移民分半間房,每間不足8平方米。當時,小孩多的家庭只能好幾個人擠一張床。帶著豬、羊的人家,沒地方建圈棚,只能白天拴在門外,晚上拴在床頭。
移民接待站為每戶人家準備了兩百塊壘灶的磚、三十斤蘆葦柴火、一個藍墨水瓶做的煤油燈和18塊錢的搬遷安置補助。
一些來得早的移民嘗試種了小麥,卻沒什麼收成。“種下一葫蘆,收不上來半瓢。”全淅林説,蘆葦的根扎得很深,砍了挖了沒多久又拱出地面,把小麥全給蓋住了。
那些來得晚的移民沒來得及開荒種糧,1968年10月份搬到大柴湖時,移民楊俊道從老家帶了300斤幹紅薯片,剛過完春節就已經吃光了。當年,楊俊道和很多移民一樣只能買國家統銷糧。楊俊道吃了三年的統銷糧。當時每個成人按27斤/月憑證購糧,很多移民拿不出錢,只能先把糧證賣了一半換成錢,再買糧食。
為了省點吃,一些移民把糧食磨碎了,本來一份粥的米分成幾份煮,還有一些人只能薅來柳芽和榆錢,和上幾顆糧食蒸著吃。
吃水也是問題。大柴湖是個水窩子,卻缺幹凈的水。井裏打出的水,看著清澈,白毛巾、白衣服一洗就染上一片黃。這水一煮開全是白沫,喝著還有一股難以下咽的腥臭味,連煮水的鍋也結著厚厚一層水垢。一些移民為了喝上幹凈的水,去“刮”淺淺的堰塘裏的水。
其實,大柴湖是咬著牙扛下安置移民任務的。一位移民接待幹部回憶,移民安置工作壓力巨大。大柴湖移民接待站的幹部甚至買光了周邊磚廠的磚。當時大柴湖實際安置的移民人數遠遠多于搬遷前統計的數量,面對背井離鄉的移民,大柴湖不得不想盡辦法安置。
大柴湖移民的問題很快得到了湖北各級領導幹部的重視。當時鐘祥縣移民指揮部副指揮員黃益洲索性就駐扎在大柴湖。每次下雨他就拄著木棍蹚著水,組織移民們排水,和移民們一樣滿身泥巴。
但是限于財力、限于當時的國情,彼時地方也難以拿出更多的資金來一下子解決大柴湖的問題,只能一邊逐步解決,一邊鼓勵大柴湖移民自力更生,艱苦奮鬥。
“大柴湖是要變的。”絕大部分移民還是選擇改造大柴湖,在這裏安家。這時候,人們在一些屋子的墻上用石灰漿刷上了“戰天鬥地,人定勝天”的標語。
“刨掉地裏的蘆葦根,治理好天上來的水,好日子就來了”
到大柴湖的第二年,移民們開始開荒蘆葦蕩。
大柴湖的蘆葦是實心的,又粗又硬。老百姓喊這種蘆葦為“鋼柴”。那時楊俊道每天天不亮就下蘆葦,直到腰都伸不直,胳膊也抬不起來才回家。即使這樣賣力,好幾天他才砍了一小垛。
砍“鋼柴”確實累,得一根根地來,還得隨身帶著一塊磨刀石,沒砍幾下就得磨一會刀。一些移民索性搬個小板凳,坐著砍,沒一會板凳就陷進泥裏了。那些不小心踩到了留在地面上鋒利堅硬的蘆葦梗的,甚至被戳穿了腳。
砍過的蘆葦地,得刨出蘆葦根才能種地。盤根錯節的蘆葦根又深又硬,大鋤頭沒刨多久就成了“鐵和尚”。耕牛也不行,那時候牛瘦也不多,遇到蘆根,三頭牛還拉不動一張犁。
最後武漢軍區派出了75匹東方紅拖拉機,可下地沒多久,不少拖拉機就出了問題,不是犁鏵破了,就是後橋斷裂。原來,大柴湖的淤泥裏除了蘆葦根之外,還有石頭、樹根,甚至石碑。這些拖拉機也沒轍,再加上白天黑夜連軸轉,免不了出故障。
拖拉機在前面開,移民就成群結隊跟著後面撿蘆根。最忙的時候,移民村裏甚至大人小孩都去地裏彎著腰刨蘆根、撿蘆根,從夏天一直幹到寒冬。可即使這樣,第二年一些地裏還是又冒出了蘆葦來。楊俊道記得,一直這麼幹了五年之後,地裏的蘆葦才漸漸被“趕走”。
楊俊道把麥子種到地裏,可依然沒多少收成。“一畝地就只能收幾十斤的麥,哪塊地要有一兩百斤就算是豐收了。”楊俊道分析,“一是當時沒什麼肥料,二是大柴湖排水難,經常被淹,看著長得挺好的麥子,其實地下的根都爛了。”
1972年5月,楊俊道發愁收成的時候,聽到一個好消息。附近軍馬場的200畝小麥,因為連著陰雨天耽誤了收成發了霉,軍馬場索性放棄了。楊俊道和其他聞訊的移民撿了“便宜”,盡管已經變質,甚至出了芽,移民們還是小心磨成面當成寶。
再後來,公社組織移民把旱地改成水田,種植水稻。可沒多久大部分水田又改回了旱地。原來,一方面移民沒有種過水稻,怎麼種誰也不知道,當地、氣候的“脾氣”也還沒摸透。另一方面,移民們發現蘆葦地表面一層薄土,底下卻是深深的泥沙,水和肥都留不住。一些地裏打好的井也因為成本太高荒廢了。
在移民安置的最初幾年,治水和開荒造田一樣,都是頭等大事。治水得兩手抓,一手築堤防漢江水倒灌,另一只手挖渠排水免得下大雨內澇。
1967年,荊州地區調集了京山、天門、荊門、鐘祥和潛江五個縣的數萬名民工與移民一起修築了一條長達45.4公里的漢江防洪堤,耗費了土石共計6526萬立方米。這些土石足夠填滿4.5個西湖了。這麼大的工程全靠移民和民工肩挑背扛板車推。此後每年,移民都在此基礎上不斷加高圍堤。
光有圍堤還不夠。有一年,漢江又發洪災,水已經漫到了圍堤邊上,“站在圍堤上就可以洗腳了”,移民們不得不轉移到更高的地方。所幸的是,那次沒有決堤。後來,每個移民村都修建了比防洪堤更高的高臺,供移民躲避洪災,移民也叫它“保命臺”。
除了擔心圍堤之外,移民們還得“一人一把鐵鍬,下雨就往外跑”。下雨的時候恰恰是查看地勢高低、水流去向,搜尋排水渠“腸梗阻”的時機。當時鐵鍬就像每個人吃飯的碗筷一樣必不可少,大柴湖周邊的鐵鍬都賣斷了貨。
為了給大柴湖積水找出路,除了數不盡的小溝渠之外,移民們還在大柴湖東西面挖出了兩條22公里長的主幹渠,9條總長近百公里的支渠,還修建了兩座排水閘。
挖渠排水工程是從1970年開始的,挖了七八年。挖渠排水一年四季都得幹,甚至大年初一也不得閒。當時沒有橡膠雨鞋,挖渠得先脫了解放鞋赤腳上。全淅林記得,1972年冬天一場大雪之後,人被凍得直哆嗦。一條趕工期的排水渠挖到一半,溝裏除了雪水就是冰碴子。大家都在猶豫下不下的時候,時任大柴湖黨委副書記的宋育英喊了一句:“共産黨員跟我上。”就下到了刺骨的溝裏汲水,沒一會她的腿就凍成了“紫蘿蔔”。其他人也跟著卷起了褲腿。
“刨掉地裏的蘆葦根,治理好天上來的水,好日子就來了。”大柴湖移民挖渠築堤、刨蘆墾荒時,喇叭裏的廣播就這樣給移民們“打氣”。經歷了約10余年的“戰荒湖”,原來的蘆葦蕩成了莊稼地,一下雨膝蓋都陷進去的沼澤路也變成了石子路。
“要和本地人結婚,差點被拘留了”
1976年春節剛過沒多久,移民曹明光就差點被法院拘留了。
起訴他的是吳健美的父親。吳健美是他的相好,也是湖北鐘祥本地人,長得漂亮。當時19歲的曹明光模樣也俊,像當時流行電影《偵察兵》男主角王心剛。春節拜年時,兩人在曹明光姨媽家一見鐘情。
那時移民過得確實不如當地人。一些當地人瞧不起移民,本地人不願意和移民處對象。
曹明光和吳健美處對象的時候,本地人甚至已經能穿“的確良”衣服了,而大多數移民一年到頭都是一件黑粗布衣服。那件黑粗布衣服原本是解放軍捐給移民的棉服。天熱了,移民就把棉花扒了當單衣,等到天冷了再塞上。
曹明光當時連像樣的衣服都沒有,吳健美第一次到他家的時候,他的床頭還拴著豬。年輕剛烈的吳健美沒有嫌棄曹明光,可她父親卻不同意移民當自己的女婿。見攔不住女兒往曹明光家跑,他索性一紙訴狀告曹明光拐賣了吳健美。
法院和派出所到府找曹明光的時候,他剛好外出,只留吳健美一人在家。
“這不是曹明光的錯,新社會,我看上了他是我願意的。要抓抓我。”吳健美説。
“這是你爸爸告的,你跟我們回去把問題説清楚。”
曹明光認定了吳健美,他索性借了一身當時時髦的白上衣、藍褲子和白球鞋,上她家裏去。見曹明光的幹凈模樣並非印象裏移民形象,再加上女兒是鐵了心,吳健美父親最終同意了這門婚事,卻不願出一分錢嫁粧。
曹明光娶吳健美,成為移民娶本地人的第一例。在此之前,除了土地糾紛摩擦外,雙方幾乎不來往,甚至連本地幹部也不願意來大柴湖任職。
上世紀80年代當了大柴湖黨委書記的楊俊道説,當時鎮裏本來要調來一個本地人當婦女主任,可她一聽説是到大柴湖來,寧願被開除也不幹。原來,她不完全是嫌大柴湖移民窮,也因為聽不懂移民説的河南話、吃不慣移民喝的苞谷粥。
曹明光和吳健美成了“名人”。一些本地人和移民開始“效倣”他倆,再遇到阻礙時,有人就説:“曹明光都結婚了,我們怎麼就不能呢?”
可全淅林説,本地人和移民的融合光靠一兩家結婚不管用。改革開放前,大柴湖本地小學、初中、高中一直都有,當時勞動力也不像現在這樣自由地流動,再加上本地人和移民時不時有摩擦,移民一代和大部分移民二代就在相對封閉的移民社區裏學習、工作和生活。以至于大柴湖的高中被撤銷之後,移民三代不得不去鐘祥市裏上高中時,才發現自己和本地人説的話並不相同。
“這種集中安置的移民搬遷模式,一方面有利于保持移民原本的風俗習慣,另一方面卻不利于移民融入當地的社會中去。”全淅林説,“真正的融合是改革開放之後,移民生活逐漸好轉,和本地人交往變得頻繁之後開始的。”
正把“柴湖”變成“財湖”
1995年高中畢業之後,移民二代馬強到鐘祥跟著一位老師傅學廚藝。當時一口河南腔的馬強還被一起學藝的本地學徒嘲笑了。等到幾年前,自己的孩子到鐘祥上學時,“幾乎沒有本地人和移民的觀念了,更談不上誰瞧不起誰了。”
馬強記得明顯的轉變發生在2000年前後。那時候,移民的蘆葦房變成了磚瓦房,再後來變成了樓房。大柴湖的變化惹得本地人也羨慕:“大柴湖真的不一樣了。”
在大柴湖一些移民村裏,還保留著一兩間加固過的蘆葦房和一些過渡房。
上世紀80年代初,父親馬季洲用泥巴混上麥糠建了2間土偏房。當時,馬強和哥哥姐姐個頭長得快,那間唯一安置房已經住不下了這麼多人了。每次一刮風下雨,母親怕偏房塌了,就趕緊喊住他們出來。
到了1989年,這幾間泥巴房、蘆葦房換成了紅磚大瓦房。“1982年分産到戶之後,移民們開始發展副業,多種經營。”馬強解釋,“與此同時,哥哥姐姐們也都南下打工,吃飯的少了,掙錢的多了。”
1983年,大柴湖黨委書記楊俊道提出“立足八分地,打好翻身戰”的口號。移民從每人平均八分的地裏挖出的第一塊“寶”是麥冬。麥冬喜歡沙地,種植技術也不難,當時每公斤價格在二三十塊錢左右。不少吃螃蟹的移民嘗到了甜頭。
移民從地裏挖出的第二塊“寶”是蒜薹。大柴湖種出的蒜薹成熟早,産量也高,每到蒜薹上市的季節,山東、河南、陜西、新疆等各地的收購商就涌進大柴湖。一些蒜薹甚至遠銷日本、韓國。
一些人不甘心在土裏刨食,把家門一鎖,背上被褥外出務工。馬強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打工一年能有一萬多塊錢的收入。曾經有一段時間,留在家裏的家長們在郵局門前排長隊,等著取外出務工的子女寄來的匯款。
改革開放初期,移民外出打工比本地人多得多。”全淅林説,“越窮的地方出去的越多,貧困逼得人沒辦法。”在上海,甚至出現了“小羅城”,羅城是大柴湖一個村。
2004年,鐘祥開始給大柴湖“松箍”——組織部分移民自願搬遷到縣內其他鄉鎮,緩解大柴湖移民人多地少的發展瓶頸。為了讓移民安下心,縣裏給每戶移民在新安置地蓋好了瓦房,並承諾給予移民和遷入地居民相同規模的耕地面積。
從大柴湖鎮曹寨村的移民曹明虎,遷入冷水鎮董溝村之後,分到了7畝多良田,又承包了當地70多畝耕地,兩年不到就買了夏利小車跑客運,讓許多不敢搬的移民眼饞。
2006年,馬強把家裏用了幾十年的挑水扁擔和“壓把井”的龍頭收了起來。當年年底,大柴湖新自來水廠正式供水,移民們告別了喝了幾十年卡喉嚨的腥臭地下水,漢江水通到了每家每戶。丹江是漢江的支流。通水的那天,一位70多歲的移民説,壓根沒想到自己還能喝到老家流來的水。
2014年1月,湖北荊門大柴湖經濟開發區挂牌成立,成為湖北省最年輕的省級經濟開發區。從那時起,汽車制造及零部件産業園、光電子産業、精品花卉産業逐個在大柴湖安家,移民們在家門口也有不錯的收入。大柴湖逐漸變成“財湖”。
“從前窮出了名,很多人不好意思提自己是大柴湖人。現在大柴湖發展得比本地鄉鎮還好,不少人覺得挺自豪。”馬強説。
共飲丹江水
全淅林的老母親去世前,一直念叨著回淅川老家去瞧一瞧。可當時經濟條件差,交通也不方便,得一路顛簸折騰,怕母親身體吃不消,所以一直沒能成行。
上世紀80年代,淅川和大柴湖通了直達的客車,每天只有一趟。當時返鄉探親的移民絡繹不絕。
有一回,幾個年輕人背著一個老移民上了這趟客車,一路神色緊張。直到下了客車,司機才發覺老人已經去世了。原來老移民生前唯一的願望就是回淅川看看,死後把自己埋在淅川的高坡上。
盡管搬來大柴湖51年了,楊俊道和許多一代移民一樣,始終認為自己是河南人。現在楊俊道還是只會説河南話,日子也按照河南的過法來。
這樣的“河南特色”正在移民二代和三代身上褪色。楊俊道的孫子楊凱(化名)見本地人能説些本地話,在家能説些河南話,在學校説普通話。而在飲食上卻更接近湖北習俗,吃米飯,喝米茶。
有一年清明,楊俊道領著全家回了淅川掃墓。那時楊凱還小,楊俊道指著水庫對楊凱説,“咱們家以前住的地方就在水裏面,為了建丹江口水庫搬走了,咱們的貢獻是不是很大?”
全淅林曾問過在外務工的移民二代認為自己是河南人還是湖北人,很多人説不上來,只説自己是大柴湖人。
為了讓移民後代知道“他們從哪裏來”,從上世紀末開始,曾任大柴湖文化站站長的全淅林開始有意識地收集移民口述史。2005年,全淅林出版了《移民大柴湖》一書。一位在外打工的移民二代給全淅林發來短信説,“以前甚至不敢承認自己是大柴湖移民。讀了您的文章,才知道心中的陰影是我們不了解歷史造成的。”也有本地老戶看完主動對全淅林説:“是你給我們補了一課,看完我才知道什麼是移民。”
去年12月,全淅林念叨了好幾年的移民紀念館正式開工。全淅林打算在紀念館的一面墻上寫上“舍家為國,團結奮進”幾個大字。全淅林説,“當初四五萬移民來到這片荒蕪的蘆葦蕩,要是沒有這種精神的話,人早就垮了。”
楊凱覺得自己爺爺那一輩人“很有勇氣”。他也問過楊俊道,當初從老家搬過來後不後悔。楊俊道説,南水北調是國家需要,現在大柴湖建設得也挺好。
2014年12月12日,南水北調中線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河南淅川正是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核心水源地和渠首所在地,既是“大水缸”,也是“水龍頭”。當時,楊凱已經在北京一家醫院工作了。楊俊道激動地對他説,“我吃的是丹江水,你吃的也是丹江水,咱們吃的還是河南水。”(記者張典標)

-
大數據"坑熟客",技術之罪需規則規避
2018-03-02 08:58:39
-
高品質發展,怎麼消除“遊離感”?
2018-03-02 08:58:39
-
學校只剩一名學生,她卻堅守了18年
2018-03-01 14:40:53
-
有重大變動!騎共用單車的一定要注意了
2018-03-01 14:40:53
-
2018年,樓市會有哪些新變化?
2018-03-01 0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