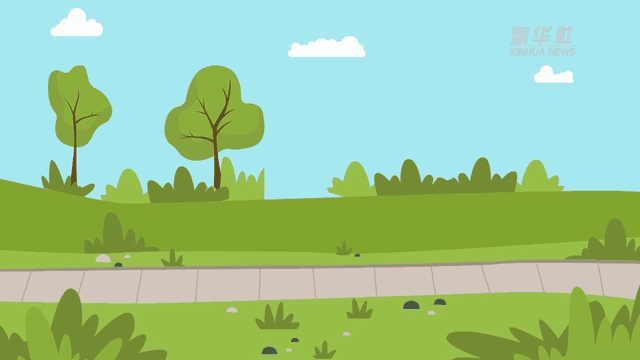《窺探》及其番外篇《窺探:捕食者》無疑是今年韓劇年中、甚至是年終盤點時,不可繞過的重要一章。
“如果可以通過胎兒基因檢測是否為精神病患者,肚子裏的孩子被確認是患者,您是否會選擇生下來?”《窺探》延續了韓劇近些年流行的高設定,直接將效果拉滿,在開播之初便將觀眾的興趣拉至最高點。
該劇的英文片名《mouse》似乎更切近該劇的氣質內核:小白鼠。劇中主角鄭巴凜作為“惡二代”是其父親“換腦手術”的實驗對象,導演崔俊裴開集便用一組蛇與鼠的鏡頭給出了故事的隱喻。在我們的常識中,蛇是鼠的天敵,然而,鏡頭下卻是老鼠咬了蛇。劇外,編導與觀眾一起,隨著劇情的推進共同進行一場社會思想實驗:惡究竟是先天基因的締造?還是能被後天環境所改變?
具體來説,《窺探》的設定是這樣的:如果精神變態的基因可以從胚胎狀態中檢測出,被識別出攜帶此基因的胎兒有99%的可能是共情閉合的變態殺人狂,剩下1%的可能是:這會是一個天才。這個幾率要不要賭?敢不敢賭?
如若不敢賭,由此通過墮胎法案,涉及的是胎兒是否有人權的倫理問題。尤其,對于法律層面與宗教層面都反對墮胎的韓國來説,這一思想實驗與現實的語境發生著粘連,並具有十分切實的指向性。女性是否對自己的身體享有權利?胎兒又能否算“人”?在2020年的韓國,除一些特殊情況之外,女性墮胎仍會面臨刑罰,有關墮胎的合法化問題的討論也一直處在輿論的中心。
如果要以99%絕對的、壓倒性的大多數去抹殺掉那1%的生存權,這種邊沁式功利主義的做法,將所有的價值都表述成一種通用的貨幣價值。用99%與1%精確地比較利益、計算得失,如此做法意味著冰冷地計算犧牲與代價。
可是,選擇犧牲誰?誰又“應該”被犧牲呢?這個“應該”又有誰有審判的權利呢?
這個經典的“電車難題”,被裹上了一層軟科幻的外殼,再次被推出。尤其,劇情還燒腦地夾雜了兩個“惡二代”,究竟哪一個才是真的變態兇手?是看起來情感淡漠的醫生?還是正直的新人刑警?能否有人能夠打破99%的魔咒?懸疑之上再疊反轉,甚至于魔幻地安排了腦前額移植手術,換腦後劇集的重重迷霧又濃了一度。
《窺探》首先拋出來的全民選擇是,25年前,轟動一時的殺人案後,以一票之差,最終未能通過墮胎法案。然而,當時間線拉到25年後,當時幸存下來的、攜帶精神病態基因的兩個孩子長大了,震驚全國的連環殺人案又再次發生,兇手是他們中的哪一個?變態殺人犯的孩子,是不是必然會長成一個殺人犯?這種宿命式的“被預判了的預判”,是否還有翻盤的可能呢?
犯罪預防,這樣的社會思想實驗,一直是創作的熱門命題。不止韓劇,遠到菲利普·迪克與斯皮爾伯格的《少數派報告》的預知犯罪,近到號稱“社教派”的臺劇《我們與惡的距離》……疑罪應當從有還是從無?犯罪預警的警戒線應設置在動機還是行為?
又該如何面對和理解“純粹之惡”?《窺探》故事的第二層同樣在于此:當我們定義“法”時,是選擇實證主義的絕對中性之法?還是選擇非實證主義的、包含了良與惡之判定的、正義絕對性的法?
精神變態的殺手,固然在腦科學的研究層面被部分地驗證存在著基因缺陷,或是腦神經共情回路的閉合。但後天的環境,社會的環境能否將這株“惡”結出天才之果,社會的悲劇能否有挽回的機會?因為共情缺失導致的先天人格障礙,會不會必然引發後天的“惡”?基因就如同人搭載的出廠設置,如何編寫自身的“程式”還要看現實代入的公式如何,就這樣,《窺探》的敘事野心又想將“社教派”納入囊中。
當然,這還源于故事的構思來自韓國一個真實的案件,2017年仁川發生了一起慘案,“仁川小學生被殺事件”,虐殺女童的是一個19歲的女孩。當被問及有何遺憾時,她在被害者家屬面前回答道,“天氣這麼好,我卻無法出去欣賞櫻花”。而《窺探》結局處作為“惡一代”的韓書俊説了同樣的一句臺詞:“這種天氣還不能去賞花,好傷心”。在社會悲劇面前,人們的理性與認知會找尋一種“合理”的回答。所以有了種種面向“惡之因”“惡之花”“惡之果”的思考。
隨著故事展開,解謎的線索逐漸深入,懸疑與軟科幻的殼子層層剝落後,故事的內核還是韓劇的三板斧——在愛的呼喚與反思中去講:人有選擇。這樣,兜了一個圈,《窺探》故事似乎回到了2020年熱門韓劇《惡之花》的回答:男主父親的殺人犯基因,如同鎖在他血管上的詛咒,但他仍在與妻子的愛中一次次地與命運抗爭,最終獲得了成功。不過,主人公鄭巴凜將《惡之花》的社會思想實驗向前推進了一步。
換腦手術的魔幻設定,新的大腦讓故事主角擁有了再選一次的機會,“我是誰”,我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鄭巴凜身上被涂上了一層追問自我的色彩,這個包含哲學式掙扎的角色極易讓人跳戲到《拆彈專家2》中劉德華飾演的潘乘風,失憶後被“洗”為一張白紙的潘乘風,在做好人與做壞人之間反覆橫跳。他的選擇,善惡一念之間,“信,就是警察;不信,就是恐怖分子”。關鍵在于,信念與選擇。而人之為人,就在于人有選擇。
類似的,《窺探》的結局處編劇讓鄭巴凜與兒時的自己相遇,讓這個沒有共情能力的殺人狂,能夠懺悔、感受痛苦、希望贖罪。他向上帝祈禱不想變成怪物。圖窮匕見,劇情的重點再次轉了個圈兒,編劇最終的企劃意圖終于露出:將對現實的思考嫁接到了心靈與信仰的力量上,最終解決的辦法在于懺悔之心。
在極限設定裏“狂飆”、經歷三次急轉彎的強反轉,可以理解為是劇情的起伏與懸念。同時也暴露出了編劇駕馭高設定故事的短板,倫理、科學、社教、宗教……《窺探》可以算是麥基所説的以情節見長的“大故事”,然而,這個大故事內裏是“設定”撐起來的虛。似乎只要當敘事節奏足夠快、反轉足夠多,觀眾便可無暇去細究其合理與否,可謂是一力降十會。
然而,一個好的故事不見得是“大故事”。比起對角色人性幽暗處濃重的描摹,《窺探》花在懸疑之“骨”銜接上的筆墨顯得過于簡筆畫、太兒戲了。精彩的設定可以撐起“炫技”,卻也容易讓角色成為在極限設定裏“跑酷”的工具人,再次去人性化,從而失去獲得觀眾真實感的投名狀。可以説,若繼續向極致浮誇的“天空之城”攀登,韓劇那些關注的現實問題必定會被再次“折疊”。
韓劇《窺探》顯然走的是復制美劇的模式,但這類懸疑罪案韓劇還有“回頭路”可走嗎?還是只能將“跑酷”進行到底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