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中國當代文壇具有廣泛影響的著名評論家,孟繁華20世紀80年代步入文壇,即引起關注。自90年代以來,他的《文學革命終結之後——新世紀文學論稿》榮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眾神狂歡》《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卷)等主要著作至今仍然深刻地影響著當代文壇。
一直以來,孟繁華以樸素的評論之筆,開掘當代寫作的更多可能,他的不少文章令眾多文學愛好者津津樂道。
前不久,在《草原》舉辦的生態文學論壇上,孟繁華接受了北京青年報記者的獨家專訪,聊了聊關于文學以及文學批評的那些事兒,並回憶了過往求學、讀書的人生經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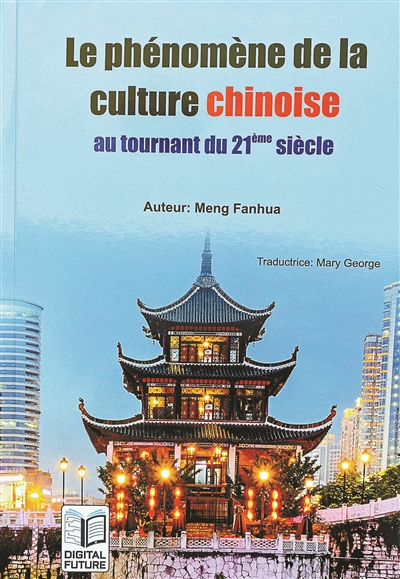
不再寫詩,認認真真讀書寫文章
北青報:您1951年出生在吉林,在那個年代,最初是如何開始從事文學批評的?
孟繁華:我的祖籍在山東。爺爺那一代人闖關東走到了吉林敦化市。爺爺一生坎坷,一輩子背著歷史反革命的罪名,非常卑微、非常恥辱地活著。他去世後第二年才被平反。我是林業工人子弟,父親是一個普通的林業工人。1968年我初中畢業就下鄉插隊了。
1978年國家恢復高考,我報了三個中文係,結果被錄取到了東北師大歷史係。後來轉係轉到中文係。過去我很想搞創作,寫詩。係主任卻告訴我,中文係不是培養詩人和作家的,是培養學者的。聽了老師的教誨,我就不再寫詩,認認真真讀書寫文章。學術研究,走進去之後,興趣是最好的老師,開始發表了文章,周圍同學都很羨慕、驚奇。那個時候不知道天高地厚,寫了很多,心裏飄飄忽忽。但確實逐漸對文學評論産生了興趣。
北青報:從歷史係轉到中文係,還是有不小跨度的。
孟繁華:我被錄取到東北師大歷史係,亞述學的創立者林志純先生就是這個係的教授,他在學界人人皆知。他給我們上課的時候已經67歲了,上課沒有教案,也沒教材,舉著個粉筆就開講。但林先生是福建人,他的普通話我一句聽不懂,聽亞述學就跟聽天書似的。我中學學了幾天俄語,到歷史係是學英語,那時一個英文字母我都不認識,老師就在課間休息時教我認字母。對我來説,專業課困難、外語也困難,那段時間完全是創傷記憶,打擊非常大。
于是我去找教務處,那個時候學校特別負責任,教務處處長勸我説歷史係是教育部的重點科係,想考上都不容易,你怎麼還要轉呢?我説我聽不懂,他説聽不懂就對了,來大學就是學習的。我又堅持了一個月,還是聽不懂,我又去找他,“老師,你要不給我轉係,我準備退學了”。他很驚訝,“都到這種程度了,坐下我們聊一聊”。他問我熱愛中文為什麼報了歷史係?我説我報的北大中文係、吉大中文係、東北師大中文係,可能是我的考分較高,就分到了歷史係。可是學校沒有轉係的先例,我垂頭喪氣地走了。我感到非常絕望,就拿著曾經發表的詩歌和文章找到中文係主任馮先生,他也認為歷史係比中文係還有影響,我説,“老師不是這麼回事兒,主要我聽不懂,不能轉那我就退學了”。我當時真是這麼想的,説得很決絕。一個星期以後,學校通知我轉到了中文係。
轉到中文係,又改成學日語,我還是一個字也不會。老師又在課間教我平假名、片假名。不過到中文係就踏實了,中文係的課程對我來説不是難題。等到期末考試,我們年級二百多人,日語我考了第一,滿分。任課教師非常驚訝,經常講我這個例子。東北師大有一大批老教授,學術氛圍非常好,圖書館藏書也很豐富,我覺得從那以後我的人生發生了變化。
北青報:您剛才説到1968年下鄉,那十年的插隊經歷對您來説有哪些深刻記憶?
孟繁華:回過頭來看插隊經歷,和當時的感受已經完全不一樣了,歷史一旦進入敘事,就有很多虛構成分。現在回想起來,剛剛下鄉的時候我們興高採烈,覺得自由了。那時候的農業生産就是前現代的鋤頭、鐮刀、牛車、馬車,剛到鄉下我們認真向農民學習生産勞動,非常辛苦但很虔誠,大家幾乎都是全勤。
過了一年之後心態就發生變化了,覺得前途非常渺茫,大家幾乎同時在一個早上消沉了,平時交流説話明顯少了。特別是兩年以後開始陸續招工、參軍,每次我都因為政審不合格被刷下來。每個同學離開,其他同學都非常難過。離開的同學雖然很高興,但心情也復雜。
幾年之後,我們集體去了林場。從某種意義上説,在林場的生産勞動更艱苦,長白山冬天的極端溫度能到零下三四十攝氏度。但是心裏總升起一些希望性的東西,比如身份變成了林場工人。其間我曾被推薦工農兵大學生,但因為家庭出身去不了。那一段對我來説是人生比較艱難的時刻。
寫一本書三個月,一篇文章寫三年
北青報:您後來進入北大學習,也是重要的人生轉折點吧,有哪些難忘的人和事?
孟繁華:1982年我畢業時,係裏曾動員我留校,但我內心潛在的理想還是去北京。我後來檢討,雖然1982到1984年我也發了很多文章,接觸到很多景仰已久的比如謝冕、洪子誠等學術前輩,以及李陀、鄭萬隆、陳建功、賈平凹、路遙、張抗抗等知名作家,但那時我還是在專業的週邊寫文章,不能進入文學討論的核心話題。嚴格意義上説,80年代在整個文學場,我是個圍觀者,還不能稱為一個地道的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者。1989年我到北大中文係做了兩年高級訪問學者後,考取了謝冕先生的博士研究生。這三年對我人生的改變非常明顯,我理解了學術和批評是什麼,也逐漸融入到核心話語的討論中來。
當時謝先生以“北大批評家周末”的方式來組織他的教學,除了博士生,訪問學者、外校教師等來參加的人非常多,大家就專業的報告展開討論。這個學術沙龍從1989年開始一直堅持了十年,我畢業後到社科院工作還經常去參加活動。
北大和謝先生這種完全開放性的教學方式,讓不同的思想、不同的觀念交融碰撞,同學之間也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所有參加“批評家周末”的人心無旁騖,一心向學。它培育了學者應有的精神和氣象,這些經歷對我影響很大。
北青報:您成名在90年代,包括獲得魯獎等一係列重要獎項,是有怎樣的機緣呢?
孟繁華:1995年我從北大畢業後去了社科院文學理論研究室,後來又調到當代室。可以説我的主要研究成果都是在社科院時完成的。當時所裏面有一批非常好的理論家,蔡儀先生是第一任室主任,還有王春元、錢中文、杜書瀛、何西來、毛崇傑等先生,他們的學術成果、治學態度都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我。當時還有像汪暉、陳曉明、蔣寅、李潔非、靳大成等很多很好的學術朋友,大家見面基本都是在談讀書。所裏經常有來自世界或全國各地優秀學者講學,這種學術環境是別的地方所不能夠擁有的。在國家核心的研究機構工作,那種精神狀態、自我期許是不一樣的。
我在學術上主要做兩方面的工作,一個是文學史,一個是當下文學批評。當下批評也包括當下文化,比如《眾神的狂歡》那本書大眾影響比較大,國內有三個版本,今日中國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被翻譯了英文、法文、日文、韓國文、越南文等。其實這本書我三個月就寫完了。我更花工夫的還是文學史,包括學術史。比如當時我參與做的一個國家重大項目《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我寫的第三篇,在社科院圖書館、教育部檔案室查資料,花了三年多時間。
北青報:現在不少學者、作家都在研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比如有“文學黃金十年”的提法,您是如何回望的?
孟繁華:對于上世紀80年代的回顧和檢討,我現在覺得學者和作家們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我更懷念的是80年代的文學環境和氣氛,以及為一個觀念或問題爭論得面紅耳赤的誠懇和坦率,而不是説那個時代是無可挑剔的,這種想像是不切實際的。80年代最迷人的不是説文學的讀者多,文學多麼重要,而是説80年代有一個自由、開放的文學環境,大家對文學懷有一種信念。
上世紀90年代、具體地説是1993年,上海學者發起非常重要的人文精神大討論,對于厘清那個時代的價值觀、主要問題和矛盾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學創作上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出現了以賈平凹、陳忠實、高建群等“陜軍東徵”為表徵的文學。
上世紀80年代的理想主義或樂觀情緒,後來逐漸開始沉淀,對研究的學術性的強調開始逐步成為一種自覺意識,這點非常重要。但是這個時候也有一些非常熱的文化熱點出現,比如陳寅恪、吳宓、王小波、顧準等人物被津津樂道,出了很多書籍。這些“熱”的背後隱含著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另一種訴求。這就是,他們才是知識分子應該選擇的道路。這當然也是一種幻覺,任何時代知識分子道路的選擇都是自由的。
真正的文學批評,需要與“高端”對話
北青報:具體到文學批評,您有哪些比較深刻的體會,您覺得它的意義在哪?
孟繁華:關于批評,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批評比較誠懇,作家的承受力也比較正常。那時候有的作家面對很嚴厲的批評,會很苦惱、很痛苦,但不會因為文學批評而産生個人之間的恩怨。
後來,我覺得文學批評有兩個現象是不正常的,一是文學批評變成文學表揚,大家都是在表揚;還有一種是惡意的攻擊,甚至是人身攻擊,我們都經歷過。這兩種現象對我們批評的傷害非常大,特別對年輕人的影響非常強。
現在非常學術化地去批評一個作品或一個作家的,幾乎沒有。我實事求是地説,現在公開説哪個作家哪個作品有點問題的話,那個作家不是説痛苦,可能會是一種憤懣,一種極端的不快,這個文學環境太不正常了。要是沒有善意的批評或者實事求是的批評,那文學批評的存在還有價值嗎?
北青報:批評家與作家似乎有著天然共生的關係,您評判作品時遇到人情稿怎麼辦?
孟繁華:你這個問題很尖銳。我個人就在這樣一種文學批評的環境裏面,不可能不受到這種影響。確實有一些過去的老朋友,還有雜志社、出版社,我們年輕的時候他們都認真地扶持過我,現在人家説有個作品讓你給看一看,寫篇文章,我不可能無動于衷,評價作品的時候就不那麼客觀,好話説得會更多。
北青報:您如何評價當下文學?
孟繁華:評價任何時代文學最重要的一個尺度,是看這個時代文學的高端成就。比如現代文學我們有了魯迅,這就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國家的高端成就。對文學的期待,不要像對經濟的期待那樣:每年的GDP要不斷攀升。文學不能一年一年地看,像收莊稼似的。看任何一個時代的東西,一定要看到高端成就,就像我們看法國要看雨果,看英國要看莎士比亞,看美國要看海明威,看日本要看川端康成,看俄國要看托爾斯泰……這些文學的高峰都是世界共同的文學遺産,有世界影響的作家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標識。
實事求是地説,基數更大作品是消費性的東西,和處理人的思想情感和精神世界是兩回事情,它不代表這個時代的文學成績。高端的東西,我們要跟他展開對話,和余華、劉震雲、劉恒、鐵凝、蘇童、歐陽江河、西川……不管是嚴肅文學還是大眾文學,跟高端成就展開對話,才能真正和我們這個時代的優秀文學和文化成果構成關係,形成真正的文學批評。
北青報:近幾年,出現不少新的寫作文體,比如近來大熱的生態文學、自然寫作,對此您怎麼看?
孟繁華:文學藝術在不斷發展過程中肯定會産生新的概念、新的形式,在固有的詩歌、小説、散文、戲劇、報告文學等文體不能滿足文學創作要求時,有些刊物、批評家、作家就會提出一些新的概念。重要的是,任何一個概念和一種文體的提出,要靠它的創作實踐來證明、來驗證。像非虛構寫作到現在大概有十多年,已經成為相對成熟的一個文體。
自然寫作一直存在。從《詩經》的《關雎》《蒹葭》開始,人與自然的關係一直存在。現在重新提出,是更多人看到了現代性發展過程當中的問題,或者説,“現代”的實現是以自然作為代價換取的,環境污染,水資源短缺,災害頻仍,提倡者意識到自然對我們來説是多麼的重要。文學能做的就是提倡自然寫作。我覺得現在的自然寫作作為一個新的文學概念,理論闡釋還嫌薄弱。原因是與自然寫作相關的文化理念、文學觀念還沒有搞清楚。其實,這個理念的本質,還是要處理人和自然的關係。現在是模糊的,另一方面,我覺得還是有待于創作實踐去證明。
還有,我覺得要用一種客觀的態度對待自然寫作,不要抵觸,也不要盲目鼓勵。視野再擴大一點,比如歷史上有沒有這種東西,他們是怎麼處理的,創作實踐是什麼樣的?當我們把這些搞清楚之後,會建立起一個關于中國的自然文學、自然寫作的樣態。要講中國故事,講中國經驗,肯定會講出獨特的關于自然寫作的故事。
做一個正直的學者,一個盡量不講假話的人
北青報:您説話知識含量豐富,還特別幽默,日常生活中也如是?
孟繁華:我喜歡開玩笑。一個做文學的人也弄得正襟危坐,實在不喜歡。當然,這也是一種自娛自樂吧。到了一定年齡,各種事務使時間變得非常零碎。我是很無趣的人,打牌下棋都不會。偶爾和朋友一起喝喝酒就算業余生活了,其他的時間基本是在讀書寫作。閱讀積累非常重要,比如上課講到哪個作品,寫過讀過的,幾十年我都不會忘記。
做學術,假如不了解新的理論,就不可能獲得新的方法、新的觀念。所以讀書對我來説,就是活到老學到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學, 21世紀前十年,我可能算是一個重要的批評家,2010年以後,我們這一代人的影響逐漸在淡化,這是客觀事實。可能是性格原因吧,我願意跟年輕人在一起。向年輕人汲取新的觀念和思想,但也不是跟著年輕人跑。一面向著未來,一面向著過去,既瞻前又顧後才不至于和這個時代離得太遙遠。
北青報:進入耳順之年,您會怎麼看待生命,比如疾病、生死。
孟繁華:沒有刻意考慮過這個。我曾經得過嚴重的疾病,得知時有那麼三五分鐘是極度絕望的。但是很快就鎮定了。我記得很清楚,2016年3月做的手術,那天我特別輕松。進手術室的時候,我還開玩笑,説總得有一個儀式吧,就這麼給推進去,很不嚴肅嘛。手術下來,我太太説醫生説非常成功。我還跟她開玩笑,我説醫生都這麼説:下來的,説非常成功;下不來的,説我們盡力了。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很多東西可能是命定的,未知的東西,神秘的事物,但不要用無知的方式去對待它。具體到對自我的要求,就是生活裏做一個好人,做一個正直的學者,做一個盡量不講假話的人。(文/記者 李喆 供圖/孟繁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