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彥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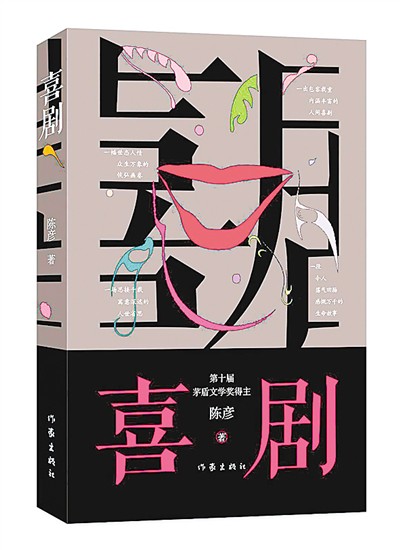
《喜劇》 作家出版社出版
2020年,由陳彥小説《裝臺》改編而成的同名電視劇熱播,人們對主人公刁順子的形象津津樂道,也由此認識了戲劇舞臺背後的特殊群體——裝臺人。時隔近一年,作家陳彥再次推出長篇小説新作《喜劇》,作為他“舞臺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與《裝臺》《主角》一起,演繹出戲劇世界的眾生相。在這部作品中,陳彥將目光聚焦于戲劇舞臺上容易被人忽略的喜劇演員,通過名醜賀少天(藝名“火燒天”)之子賀加貝、賀火炬兩兄弟曲折的學藝、演出、辦劇場之路,于世態人情之變中叩問喜劇精神、參悟人生奧秘、譜寫梨園傳奇,在密織細節中彰顯現實主義精神、講述別具一格的“中國故事”。
喜劇筆法寫喜劇故事
《喜劇》講述了賀氏一門父子兩代醜角演員的傳奇人生。父親賀少天是大名鼎鼎的喜劇表演藝術家,演技精湛且深諳喜劇之道,憑借天生異相與孜孜不倦的鑽研練就了一身絕活。大兒子賀加貝、二兒子賀火炬雖比不上父親,但從小耳濡目染,在父親的督促與言傳身教下日益成長為舞臺上優秀的醜角演員。傳統曲藝在時代大潮裹挾中沉浮不定,隨著父親去世,兄弟倆也各自開始了磕磕絆絆的人生之路。
“這個故事我寫了好多年,從十幾年前喜劇最火的時候就開始醞釀、構思。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又把它翻撿出來,銜接起斷裂了十幾年的茬口。”陳彥説。
小説開篇,長了一個“前抓金”“後抓銀”菱形腦袋的賀加貝,雖其貌不揚,卻對自己的搭檔、女演員萬大蓮情有獨鐘。因求之不得的心焦,賀加貝發起了高燒,而一旁的火燒天卻在對著鏡子做鬥雞眼,辮子一翹一翹地練功。兩相對照,詼諧幽默的筆觸立顯。
“既然寫喜劇,在寫法上也要有點喜劇色彩,我就嘗試換了個寫法。”陳彥説。在小説中,他還杜撰了一條名叫“張驢兒”的柯基犬,通過轉換敘事視角,讓它開口説話,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時也諷刺了故事中人虛偽可笑之處。
不過,幽默外表下包裹的卻是嚴肅主題。在小説題記中,陳彥寫道:“喜劇和悲劇從來都不是孤立上演的……它甚至時常處于一種急速轉換中,這就是生活與生命的常態。”
《喜劇》中,賀加貝一度背離父親所持守的價值觀,在與編劇鎮上柏樹、王廉舉、史托芬等人的合作中,逐漸喪失了自己的藝術追求,唯“笑”是從,在“邪”路上越走越遠,人生最終以悲劇收場。弟弟賀火炬卻因偶然的機緣,覺悟自省,在深造與反思中理解了“守正”才是喜劇藝術的根底,讓人生的峰回路轉有了新可能。如果説,名震三秦大地的火燒天代表著喜劇正宗,那麼賀加貝、賀火炬的分道揚鑣則象徵著時代變遷中不同的喜劇之路。
作者用36萬字的篇幅帶我們走進喜劇的世界,伴隨著萬大蓮、潘銀蓮、武大富、好麥穗、潘五福等各色人物登場,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諸般人生際遇在古城西安乃至三秦大地上演,而核心還是作家著力描繪的喜劇演員。
“以喜劇演員為主角的小説不太多。在我心中,喜劇演員是為人類制造歡樂的人,我們應該感謝他們。他們在娛樂大眾的同時,也在警醒大眾,那些鄙俗、醜陋的邪念要時時提防。”陳彥説。
重提一種喜劇精神
在陳彥心中,悲劇固然高級,但從某種程度上講,喜劇也是人類生存智慧的體現,優秀的喜劇往往代表著一個時代的智性高度。“喜劇不是嘻嘻哈哈,不是單純搞笑,一味迎合觀眾笑聲的不是喜劇。”陳彥説。
幾十年的戲劇工作經歷讓陳彥對什麼是真正的喜劇精神有了更多思考,他更從古今中外的喜劇經典中尋找醜角的功用與意義。
“醜角為戲之有戲、出戲、出彩,做了太多太大的貢獻。從古希臘到中國的宋元雜劇,他們都是重要的佐料、味精,有的甚至如高湯一般,失去了便讓戲味同嚼蠟。更別説在重要關目上戳穴、點睛、‘把南轅扭向北轍’的絕招了。”陳彥説。
他有一個比喻,喜劇像蒸汽機,啟動時表現出一種升騰與磅薄的氣象,讓人昂揚亢奮、熱血沸騰。而悲劇更像一臺內燃機,表面不動聲色,內部一旦驅動,便點火壓強了。人們總是追求“喜劇”的效果,但其實有喜就有悲,二者都是人生況味的應有之義。如何求取平衡,是《喜劇》試圖探討的主題。
伴隨著賀加貝賀氏喜劇坊生意的蒸蒸日上,潛在的危機也日益凸顯,隨著觀眾索要笑聲的頻率越來越高,賀加貝的喜劇事業也瀕臨崩壞,最後不僅透支了自己,也被觀眾所拋棄。而在陳彥看來,原因正在于忽略了喜劇應有的邊界。
“越是熱鬧的東西,越要劃定邊界、守住底線。喜劇一旦泛濫,成為我們的生活習性,尤其是希望把它變為我們的生活日常,那麼喜劇就會變味走樣,直至輕浮如魚鰾、浮萍。”陳彥説。
作者通過火燒天和南大壽兩個人物表達了喜劇如何守正創新的觀點。在臨終時,火燒天總結自己一輩子唱戲的經驗説:“一是得有點硬功夫……二是得有底線。臺下再起哄,你都不能説出祖孫三代不能一同看演出的下流話來……三是凡戲裏做的壞事,生活中絕對要學會規避……不敢臺上臺下弄成了一個樣兒,那你可就成真醜了。”而老編劇南大壽則總是在關鍵時刻不失時機地敲打賀加貝,提醒他不要數典忘祖,忘了本分。
喜劇演員、編劇、戲劇研究者、劇場老板、觀眾、故鄉人、打工者等勾勒出一幅戲裏戲外的人生百態,而作者心中的喜劇精神在讀畢全書後也呼之欲出——喜劇是調節情緒的一劑良藥,是洞悉人性弱點的一臺顯微鏡,是反觀自我的一面凹凸鏡,是留情面地敲打別人的棒槌——它在不知不覺中提升我們自己。
舞臺濃縮人間百態
17歲發表第一部短篇小説《爆破》至今,陳彥從事小説創作已有40多年。他創作的重心,始終與西安、與戲劇有關。
從1990年調到西安工作,他在這座厚重的古城住了30年。“在西安的子夜,我交朋、會友、吃喝、讀書、寫作幾十年。離開至今,夢中還是夜長安的景象。”陳彥回憶説。西安成為他《西京故事》《裝臺》《主角》《喜劇》等小説廣闊的背景。
在這裏,刁順子、蔡素芬、憶秦娥、胡三元、賀氏父子、潘銀蓮、潘五福等小説人物交相輝映,組成了陳彥筆下色彩斑斕的戲劇世界。“舞臺濃縮了歷史和現實中生命的精華。借由舞臺這個小世界、小窗口,我們可以看到更廣闊的大世界、大社會。”陳彥説。
同樣是戲劇題材,陳彥寫了這麼多卻又不重樣,顯然與他豐厚的生活積淀密切相關。
“我在劇團當專業編劇,做研究,做管理,無形中獲取了這個行當的諸多隱秘,那是無盡的歷史沉積,也是無窮的源頭活水。”陳彥説。25年的文藝團體經歷,使他的生活與創作形成了血肉相連的關係,也讓他對人性的洞察日益深刻。
“劇場是一個巨大的人性實驗室,就像宇宙是科學家探測深空的試驗場一樣,那裏會出現無限的可能性。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包括真善美與假醜惡,也像萬有引力一樣,在劇場中會相互作用、牽引。”陳彥説。
雖然“創作要扎進一塊土地”,但陳彥卻從不給自己的閱讀設限。“作家的閱讀量要大,要開疆拓土地去閱讀,不要局限于某一門類。有時候反向閱讀也會形成正向助力。”他自己家就定了很多天文學的雜志,在作家身份外,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是一位天文愛好者。
“根基要扎得深些,才能更好地仰望星空。這句話對閱讀、寫作、人生同樣適用。”陳彥説。(記者 張鵬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