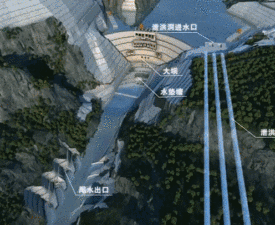攝影:邱開培
攝影:邱開培 攝影:沈慶仲
攝影:沈慶仲 攝影:沈慶仲
攝影:沈慶仲 攝影:沈慶仲
攝影:沈慶仲
時至今日,人們仍在思考、猜測著西雙版納野象北移的動機和目的。
它們是為了尋找更適合的食物?是頭象迷失了方向?是否與氣候變化有關?今後,類似的遷移會不會成為常態?這次大象的出走又帶給我們人類哪些啟迪?
出走
2020年3月,生活在西雙版納的15頭亞洲象,在沒有任何徵兆的情況下,踏上終點未知的漫漫長路。
它們是動養保護區裏赫赫有名的“斷鼻家族”。它們從密林中走來,也是從洪荒時代走出,步履間依然留存著荒野王者的氣度。它們是地球上唯一沒有天敵的動物,除了人類。它們穿越密林,一路向北,翻山越嶺,如履平地,遷徙能力之強令人咋舌。
專家學者們也無法精準判斷象群北上的終點在何處,氣候、食物、水源能支援它們走到哪裏,一切都需要一步步地監測、評估。
行進在海拔爬升的路途中,其間兩頭小象出生,三頭折返。最終野象在2021年6月2日晚間,歷史性地抵達昆明地界。在人類的謀劃推動下,這群大象一路南下,8月8日,跨過玉溪元江大橋。故園濕熱蔥蘢的密林就在前方,這場歷時一年半的奇幻旅程迎來終點,人象平安。經歷了漫長的流浪,萬物復歸原位,各得其所。
然而,時至今日,人們仍在思考、猜測著野象北移的動機和目的。
它們是為了尋找更適合的食物?是頭象迷失了方向?是否與氣候變化有關?今後,類似的遷移會不會成為常態?
也有可能是野生大象固有遷徙本能的一次覺醒?畢竟,亞洲象遷移擴散,自古以來都是常見現象。
野生動物有遷徙本能。鳥類也在遷徙,非洲大草原的很多哺乳動物也在遷徙,還有更多體型更小、更不引人注目的野生動物,都在努力找尋著自己的生存空間。在非洲草原上,在幹旱季節,野象也會往水草豐美的地方遷徙。一旦動物失去遷移能力,種群生存力會快速下降,嚴重時甚至可能局部滅絕。
引起動物擴散的原因很多,包括食物資源出現短缺,在社群和領域中處于劣勢的個體被驅逐,幼仔長大被親代驅逐,躲避天敵,追尋配偶,自然環境與氣候條件的反常變化(如生境災變或環境污染等),分分合合,有進有退是種群行為的常態,它們只是延續著自然界持續千百萬年的野性、自由和被生存本能完全驅動的單純。
英國歷史學家伊懋可在其《大象的退卻》中,通過一個動物種群(亞洲象)的遷移管窺中國環境史,讓人們意識到,大象跨越數千年、從東北撤向西南的退卻之路,對應了森林和植被的變遷,正是“中國人定居的擴散與強化的反映”,與華夏民族定居范圍擴大和農業生産集約化幾乎同步。
參與了大象北巡的具體工作,我對伊懋可的思想和觀點有了新的領悟。如果把野生動物的遷移和擴散,簡單地歸結為人象之爭或環境破壞,有趨于偏激而背離客觀真實之虞,盡管這種可能也確實存在。
生命的故事是復雜的、多樣化的、出乎意料的,並不完全是等著隔代的有心人前來串起的零散片段。
只有一點是肯定的,它們的行為一定是在各種相互制約的力量平衡作用下呈現出來的結果。
前尋:在歷史雲煙的深處
所有異象都有因果,有漫長的時間線。我試圖回顧大象遷移的歷史,努力看清它們本不為人類所熟知與關切的命運。
大象也被視為“魅力型大型動物”,自古就備受宮廷、顯貴的恩寵,具有相當的政治文化象徵意義。明清玉器古玩中“太瓶有象”這樣的祥瑞圖案,諧音“太平有象”,是對國泰民安的優雅祝福。在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廟宇、殿堂、皇家陵墓等,也常用象作為裝飾。
上古時期的舜帝,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弟就叫象。它曾經屢次陷害舜,後來卻被舜的道德力量所折服,最終“舜封象于有鼻”(《漢書》)。應該説,這則神話隱晦地反映了人與野象鬥爭的過程。舜感化象,實際上講的就是人類馴服野象的歷史。在後世民間,這個傳説還進一步成為舜帝“孝感動天”的象徵,“舜耕于歷山,有象為之耕,有鳥為之耘。”
“馴化本就是一個共生的過程,是動物和人類共同努力的結果”(萊恩·費根:《親密關係:動物如何塑造人類歷史》)。馴化後的野象極為忠誠,它們任勞任怨,表現出非比尋常的親人類甚至親社會性。象足踩踏農田、象鼻汲水灑地,比之耕牛,能大大提高耕作效率。比之“老虎與人”,人與象更能成為人類與野生動物關係的上古縮影。那時,華夏先民和亞洲象,都生活在合適的位置,並由此鋪陳開有機、連續、動態發展的交往歷程。
在雨林中,象群會推開高大的喬木,開辟林窗,尋找合適的食物。
大象的智商相當于6至8歲的人類孩童,它們能精準記住大面積區域內食物和水源的位置。它們有著獨特的思維能力,記憶是它們的地圖,經驗是它們的智慧。大象在尋找水源的路上會留下糞便,荒野中迷路的人類也會受益,他們沿著糞便走,就能找到水源。
大象生性天真,極具智慧,如藏牙、役鼻、泣子、哀雌等,這些習性無不顯示出很高的靈性。它們與人有交流感應,能領悟人的意圖,也具有知恩圖報的意識。
“有野象為獵人所射,來姑前,姑為拔箭,其後每至齋時,即銜蓮藕以獻姑。”(《撫州臨川縣井山華姑仙壇碑銘》)“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槎。人為出之,象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掊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朝野僉載隋唐嘉話》)類似這樣以象牙報恩的記載有很多。象牙在歷代均屬珍産,與明璣、翠羽、犀角、玳瑁、異香、美木並稱,很有趣的是,大象居然能認識到,象牙是人類需要和喜歡的東西。大象有將自己的蛻牙埋藏于地的習慣。將獵人引至一處,之後盡出“所藏之牙”,這樣的情節並不完全是小説家的杜撰。
古人也認為象具有仁慈寬厚、樸實穩重、忠實正直的品質。《太平廣記》中記載:“安南有象,能默識人之是非曲直。其往來山中遇人相爭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卷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這就又具有因果報應的思想了。
森林中的退隱
森林在以農業為主的生産體係中,並不被看作是一種寶貴的資源,更何況它還暗藏了包括大象在內的傷害人畜、破壞莊稼的野獸,所以越來越多的森林變成了耕地。先秦以降,中原地區的森林因人類活動而逐漸消逝。加之連年戰亂,出現了人與象爭奪生存空間的情況,“猛象出沒為患”“暴稻谷及園野”“食民苗稼”“踐民田”之類的記載在史料中不絕于縷,人類隨之進行獵殺,衝突周而復始,亞洲象的分布區域逐漸縮小。
大象所處的是更為復雜多樣的野生環境,的確更有助于揭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互動與關聯。
據《呂氏春秋》記載:“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這説明當時黃河流域還生活著眾多大象。另外,河南省的簡稱“豫”字,就是一幅人牽大象的象形畫。不過按伊懋可考證,在周代時,大象就已經從河南北部,退到了淮河北岸。這在很大程度上來自氣候變遷的影響。在西周時期,氣候還比較溫暖,大象在中原地區相當活躍,然後氣候逐漸趨向寒冷,直到兩晉時期達到冷期的極值,然後開始回暖,到唐朝時有個小溫期,在長安還可以看到橘樹,之後一直趨冷,直到明朝達到了峰值。
唐代是大象從長江流域消失的一個重要時期。從唐人筆記小説中我們看到長江流域有象出沒的記載,但實際上在隋唐時期,象廣泛生存的地區,已經主要集中在嶺南、雲南和安南一帶了。
“元嘉六年三月丁亥,白象見安成安復”(《宋書·符瑞志中》);“永明十一年,白象九頭見武昌”(《南齊書·祥瑞志》),“天監六年春三月庚申,隕霜殺草。是月,有三象入建鄴”(《南史·武帝紀上》)。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有大象從長江流域的黃阪縣(現武漢一帶)出發,經過長距離的漫遊和遷移,到達了南陽盆地,其間甚至在江北的南陽縣過冬。宋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又有大象漫遊至京師開封,最終被捕獲,飼養于玉津園中。以上兩例均發生在宋代農業開發力度加劇的時期。當時亞洲象在長江流域已極為罕見,遊走跡象也並不活躍,以至于幾個特例便被寫入正史。
明朝萬歷年間,曾經出任雲南參政的福建人謝肇淛,在記錄風物掌故的《五雜俎》中曾寫過:“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馬然,騎以出入,裝載糧物,而性尤馴。”
清晚期後,珠江流域的亞洲象趨于滅絕。
歷史是一個連續的過程,變化也是在連續逐漸積累中生成的。到19世紀30年代,廣西十萬大山一帶的野象滅絕。從此,野象退縮到雲南的崇山峻嶺中。
版納是古代“百越”的一部分,亦謂“滇越”。“百越”曾有“乘象國”之稱,如今又成為亞洲象最後的世界。
這樣看,大象的確是一路退卻的。如此龐然大物,如此強勢的物種,在與人類的鬥爭中逐漸敗退,退出了人煙稠密的人類生存區域。它們躲避弓弩,躲避獸夾,躲避鋸斷它們牙齒的利刃,躲避冰冷的鐵籠,最後反正是見人就躲,也有少數情況之下,它們會發起兇猛的集團式的絕地反擊。嚴酷的環境抑制了生命的繁殖力量,它們的數量一直在下降。
正如伊懋可所言,中國環境變遷不應只在自然科學因素,“大象的退卻”所反映的環境變遷歷史機制,其實非常復雜,“經濟形態、社會構造、政治制度、文化觀念、技術條件以及其他各種因素彼此交織”,通過不同地理條件、不同歷史分期人與動物的多元互動,來觀察和分析歷史,能讓我們在遲滯的時光之河中,看到緩慢變化的力量,一點點衝刷著古老帝國的滄桑容貌。
荒野上的環境史
有時會想,大象從雨林出發,向人煙輻輳的大城市進發,最終重返家園,這本身就是一個意味深長的佛家公案。它們風塵僕僕的行者姿態,像極了在人類居住區與野生動物棲息地之間的苦修者與擺渡人。
“道”者,道也。在雲南的深谷中,大象走過的地方都成了一片開闊地。它們在雨林中開榛辟莽,斷樹扯藤,闖出的通道即為“象道”。
在保護區內,森林保護力度增大的同時,也帶來了高大喬木,這從來不是大象的食物。植物發展得太好,頂冠層高大樹木形成了很高的鬱閉度,影響了大象賴以維生的食物。在叢林裏,大象會本能地推倒幾十釐米高的樹木,不讓這塊地方成林。對它們而言,林木不能太密。太陽基本照不進去的那些地方,大象是不會去的,進去了也要開路。
在旱季時,它們一邊行走,一邊用腳、鼻、牙齒隨處挖掘,在幹旱河床上尋找濕潤土壤。它們行走時形成的巨大腳印,成為其他小型動物使用的小型水源地。
它們大開大合,席地幕天,在自己開辟的道路上信步由韁,走州過縣如若等閒。煙波微茫,雲霞明滅,大自然每時每刻都在徐徐變幻。中華哲學的最高范疇——“道”,就藏在恍惚混沌的“象”裏。
環境一詞典出《元史·余闕傳》:“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捍,而耕稼于中”;原本的含義是“環繞居住地”。環境史有時被稱為“荒野中興起的史學”。如伊懋可所説,“環境史不是關于人類個人,而是關于社會和物種,包括我們自己和其他的物種,從他們與周遭世界之關係來看的生和死的故事。”
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類,選擇了不同的與周邊環境相互作用的方式,我們還是應該盡量避免激進的環境復古主義立場,避免令人消沉沮喪的環境原罪論,以及東方主義的偏仄視角;不必執拗地認為人類自誕生以來,或是在某種文化傳統之下,只能一直對環境施加惡的影響。從現在的情況看,人類多少是懷著一點負罪的心態,已經在努力嘗試修補與野象的關係,多少也突破了一些人類中心主義的框架。
大象北行引發浪潮般的愛心與關懷,也讓我們確信,中國環境史並不等同于“中國環境的破壞史”,而那些關于中國農民與大象無法共處、中國人等同于“環境的破壞者”、中國文化中對環境保護的感知與實際行動會永遠割裂等論斷,絕不是事實。大象北移事件後,我相信,未來人們會看到一個耳目一新的中國環境史,它將是動態的、變易的,而非一成不變的。
亞洲象的命運也發生了轉變。從全球范圍來看,由于非法獵殺、棲息地減少等原因,亞洲象的數量在過去一百年裏下降了90%。與此同時,中國境內的亞洲象數量從上世紀70年代的146頭上升到如今的300多頭。人們都也希望,大象從此找到了自己的家園,從此不再退卻,而是能隨心所往,恬然安居。
我們至今仍還沒真正弄清楚從無機到有機決定人類今天的關鍵一環。人不可能衝破圍困自己的環境樊籬以及漫長的地質時間去認識世界,從而掌握終極真理,任何人都超不出他所在的自然環境,就像他超不出自己的皮膚。
“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魯迅:《“這也是生活”》)。這正是環境史的要義,正所謂“法不孤起,仗境方生”。有一種造化的力量在塑造自然,這個力量就是共生,共生的原則就是互利。螻蟻稊稗,無處不在,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純粹的人類時刻,萬千物種共同出演著大自然導演的生命大戲。
尋歸家園
對于這次出走的象群而言,它們從始至終均在監測范圍內,一路有人照料,沒有食物匱乏之虞。相比于森林中的食材,人類一路提供的農作物熱量更高,也更可口。不止“斷鼻家族”這個象群,雲南亞洲象整體都在人類的寵愛下,正在逐漸改變食性。這是一個多少令人有些苦惱又難以改變的事實。
“人象平安”。在這個夏天裏,可以説字字千鈞,浸透著很多很多人的心血與汗水和分毫不敢松懈的努力。
誘導象群回歸,目前似乎也只是一個權宜之計。回到保護區,它們可能仍然要面臨食物短缺、棲息地不足的問題,也許有一天,它們會心血來潮,再度出發,去尋找新的棲息地。
休謨説,沒有一個科學家有能力從邏輯證實,明天的太陽一定會升起。沒有人能夠決定下一次象群遷徙的起點,但愛心與關懷,最終將決定它們未來前行的方向。
隨著生態環境進一步趨好,亞洲象種群仍將繼續增長,它們需要更大更適宜的“家”。
西雙版納熱帶雨林,是地球北回歸線沙漠帶上極為難得的一塊綠洲,被稱為動植物基因庫,庇護著萬千動物與人類。在走過漫長時光後回望,或許,這裏將是無數個生靈故事遷移、擴散或流浪的起點。潮濕的河谷彌散著夏天的味道,月光寧靜,溪流清澈,倣佛夢裏家園。在這裏,人類與自然世界之間的界限開始變得模糊。
我在這片濕潤多雨、植被繁茂的土地上行走,到處都是高聳的山脈與密集的河流。我感受著歲月深處的蒼鬱氣息,感受著千年以來亞洲象向著這裏不停邁動的腳步,蔥蘢與清澈的風景之中,心裏非常靜謐。
亞洲象對空間的需求和它們的食量一樣巨大。人類在設立保護區過程中,可能忽略了緩衝區的建設。現在,西雙版納自然保護區由動養、動侖、動臘、尚勇、曼稿5個子保護區組成,村莊夾雜其中,人口非常密集,高速公路、水電站、電網設施橫貫而過,人象混居的狀態隱藏著衝突和風險。經濟林大面積種植,提高了森林覆蓋率,但卻侵蝕原有天然林,加劇著動物棲息地碎片化。這個也是事實。
雲南的高天流雲之下,有著豐饒神秘的物種優勢和生態景觀,生物多樣性與生態整體性相輔相成。盡快建立亞洲象國家公園,把亞洲象的適宜棲息地劃到國家公園裏,為亞洲象提供更廣闊的生存空間,應是亞洲象保護最優的一種方案。
秋意深沉
半輪新月之下,巨象之蹼沉重如封印,四野瞑寂無聲。人類一步步收斂自己的欲望,叢林裏的動物重新獲得喘息的空間。
大象是陸地動物中最具代表性的符號,以其自主能動性、長期與人類密切互動等特點,成功地將全球觀者的視線引到山林藪澤,讓我們在對自然的沉思中,重新把握世界的真實容貌。在大象沉穩緩慢的步履中,人與野生動物的互動模式正在悄然更改。
三月出野外,八月歸故裏。秋天又來了。2020年一群野生亞洲大象,懷著某種令人困惑的隱秘目的,在寧靜的山野上跋涉,尋找屬于它們的樂園,去完成不為人知的使命。遙遙一千多公里、歷時一年半的漫漫長途,最後在人類無微不至的關照與引領下,在無數人的牽挂和惦記中、在不舍晝夜地守護下重返故鄉——這是對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浪漫禮讚。
盡管,大象返鄉也許並不是故事的結束。
1904年,小説家亨利·詹姆斯來到愛默生的故鄉康科德河畔時,他若有所思地説:“撒落在我身上的不是紅葉,而是愛默生的精神。”我們對萬類生靈的善意,就如那漫天飛舞的紅葉,化生在自然裏,化生在某種精神裏,如同魚出生于水中並適應水。
我們常説感謝大自然的恩惠與賜予,事實上水、空氣和陽光,並不是大自然的饋贈,而是人類誕生時的先天與先決條件。
甲骨文中的“象”字,是象形字,形似大象的形狀,後來人們逐漸將“象”字延伸,指代大象及其生活環境,隨著時日久深,再進一步成為大象存在的整個有機生態係統的象徵,常與混沌的自然界並稱,直到抽象出精神領域的“顯象”“象徵”“大象無形”這樣的自然哲學思想,被引申為大道、常理、自然規律。
《老子》有雲:“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之。”華夏民族十分重視觀察天象,“觀象”在中國古代,是關係社會治亂的大事,所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經·賁卦》)。有時“象”亦指氣象現象,比如自然四季的宏闊輪回。
蘆葉黃了,在風中酥脆幹響,和風漸漸顯露鋒芒。秋水明凈、秋空寥廓,萬物盛衰彰顯出自然輪回的本能。季節時間本質上就是心理時間,深沉的秋意喚起了人們深切的反省,四時在變幻,日月消長,正如流光飛舞,不可逆轉。然而四季又在回轉,綿延不盡,所以落花流水盡可兩兩相忘,付諸天意,反正未來可期。在這個重新降臨的秋天,讓我們一起領悟與感受,人與自然世界之間,價值與情感的核心究竟存在何方。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隨心所往,萬類自由。
(作者:劉東黎,係中國林業出版社社長、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