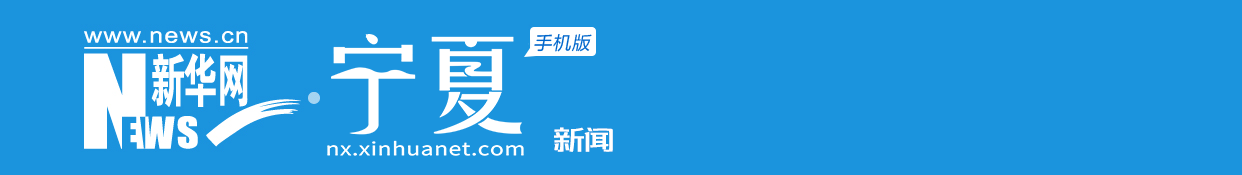刻刀輕吻石面,石屑如時光剝落,一隻靈動的青蛙在舒展的荷葉上呼之欲出……
“主刀人”是中國工藝美術大師,也是寧夏地質局培養的“塞上工匠”。他的故事,始於一把自製的刻刀,映照的卻是一整支地質隊伍的匠心傳承與精神底色。
爐火初燃:一把刻刀鑄就的匠心起點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988年,剛踏入地質局下屬賀蘭山玉雕廠的石飚,學藝的第一課竟是打鐵。

“那時候買不到現成的刻刀,閆子洋老師就領我們在小院子裏生起爐子,手把手教我們打制刀具。”石飚的記憶依然鮮活。這把自製的刻刀,不僅刻下了他的第一道線條,更將地質人“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刻進了藝術生命。
從地質局下屬的賀蘭山玉雕廠起步,三十六載淬煉,讓他從青澀學徒成長為一代大師。他的成長軌跡,深深扎根於地質局這片人才培養的沃土,他的堅守與求索,更是對地質人“三光榮”傳統和“三特別“精神最生動的詮釋。
使命擔當:兩百斤巨石的“澳門情緣”
1999年,為慶祝澳門回歸,自治區決定贈予一方賀蘭石雕。這塊重達兩百多斤的巨石,從開採到雕刻,重任落在了地質局團隊身上。
“光是把它從山上請下來,就用了七天。”石飚回憶。隨後三個月,他與夥伴們日夜圍着這塊巨石“對話”。雕一刻,轉一面,既是藝術創作,也是體力考驗。最終,《九羊啟泰·鳳歸圖》驚艷問世。這件作品,不僅是藝術的勝利,更是地質人信念的象徵,於萬千混沌中,探尋清晰的脈絡;於龐雜困境裏,堅守極致的追求。

“細節決定成敗。”這種精益求精的勁兒,不僅是石飚的匠人之心,更是寧夏地質局無數在資源勘查、找礦找水、科研攻關、野外一線地質工作者的共同畫像。
相石悟道:九層瑰寶的生命對話
“雕刻難,但‘相石’更難。”“相石”是賀蘭硯製作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為關鍵的一步。“每一塊賀蘭石都有獨特的生命。面對一塊賀蘭石石料,需要先觀察它的色彩構造,反復構思推敲,方能下刀,石飚説。他的作品《百鳥朝鳳》硯,便是他順應石料天然俏色,雕出前後九層瑰麗畫卷的傑作。青綠二色在他手中層次分明,精妙絕倫。遵循“惜料如命”的鐵律,石飚的骨子裏深深刻進了對材料的敬畏。
如今,在他的工作室裏,工作室裏,連指甲蓋大小的碎石都被妥善收藏,等待在設計中重獲新生。這種對材料的敬畏,正是地質人珍視資源、精益求精的生動體現。

薪火相傳:讓古老技藝破圈生長
“獨石不成景。”石飚深知,個人的技藝再高超,若無傳承,終將式微。他收徒授藝,七名弟子中多人已成長為高級工藝美術師和非遺傳承人。這種“名師帶高徒”的倍增效應,正是寧夏地質局人才戰略的縮影。
而他更廣闊的“講&”,在高校、在展廳、在寧夏地質博物館的“大師課”上。“每一塊賀蘭石都有自己獨特的生命,我們要做的,就是讀懂它,然後讓它以最美的姿態‘活’起來。”石飚説。
古老的硯雕走進年輕一代的視野,讓手藝的種子,在更肥沃的土壤中破土發芽。這份傳承,從一個人到一群人,正從“薪火相傳”走向“星火燎原”。
沃土繁花:一支隊伍的文明碩果
石飚手中起舞的刻刀,不僅雕刻着賀蘭石的紋路,更鐫刻着新時代地質人的精神年輪。

在他身後,寧夏地質局這片沃土上,已涌現出“全國五一巾幗示範崗”“自治區五一勞動獎章”“自治區工人先鋒號”等一批先進模範;匯聚了從自治區“塞上英才”“科技領軍人才”到“青年拔尖人才”“青年托舉人才”的骨幹力量;成功創建了3個全國文明單位、2個自治區文明單位及多個市縣級文明單位。
這是匠心的故事,更是一個集體用堅守、傳承與創新書寫的文明答卷。在寧夏地質局,這場關於精神的接力,正在塞上大地上續寫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