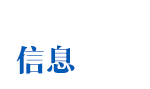在中國治沙史上,彰武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這座小城的獨特地位,與樟子松息息相關。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 王劍英 編輯 高雪梅
2024年7月24日,彰武縣章古&鎮“55秋”林(張日升/攝)
盛夏,遼寧省阜新市彰武縣四合城鎮劉家村,天朗氣清。
一大早,74歲的村民侯貴和老伴李樹媛帶着水桶、水管、鐵鍬等工具,來到自家附近的林地裏,為今年新移栽的一批樟子松苗澆水。侯貴是當地造林大戶,在過去的20多年裏,他和家人先後在2400畝沙地上種下20余萬株樹木。
彰武位處中國四大沙地之一科爾沁沙地的南緣,是一個面積3641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3萬的小縣城。
在中國治沙史上,彰武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科爾沁、渾善達克兩大沙地殲滅戰的號角,亦是在彰武正式吹響。
這座小城的獨特地位,與樟子松息息相關。
治沙功勳樹
“到現在為止,樟子松仍然是‘三北’工程乃至後面30年造林的最重要常綠樹種,”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瀋陽應用生態研究所所長朱教君語氣篤定,“沒有之一。”
樟子松,別名海拉爾松、蒙古赤松、西伯利亞松,是歐洲赤松分佈在遠東的地理變種。其樹榦挺拔,樹形蒼勁古雅,最高可達30米,壽命可達250年,具有抗旱、耐寒、耐瘠薄等優點。
它有一個榮譽稱號:治沙功勳樹
“目前,全國有超過80萬公頃樟子松人工林,分佈於‘三北’各主要片區。”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以下簡稱“中國林科院”)生態保護與修復研究所研究員、三北工程研究院特聘研究員黨宏忠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而彰武是輻射原點。”
黨宏忠先後主持的3個國家自然基金項目均落地彰武,都與樟子松密切相關。他仍清楚記得,2012年冬天第一次到彰武考察時,被皚皚白雪映襯下的高大樟子松林所震撼,“在沙地裏竟然能看到森林景觀!”
那是中國第一片樟子松引種固沙林,位於彰武縣章古&鎮,因為在1955年秋天引種成功,被當地人稱為“55秋”林。
彰武並不是樟子松的“老家”,這種樹天然分佈於大興安嶺西麓—呼倫貝爾草原的過渡帶上,和彰武相隔數個緯度,引種存活難度相當大。在探索引種之始,業界曾有不少反對聲。
1952年,遼西省林業局在彰武縣章古&鎮成立遼西省林業試驗站,開展固沙造林試驗研究。這是新中國成立最早的防沙治沙科研單位。1953年,試驗站科研人員從呼倫貝爾的紅花爾基引進樟子松種子,開始育苗試驗;1955年秋季,從長春凈月潭引種2500株樟子松苗,在沙地試栽成功,成活率達60%以上,即後來的“55秋”林。種子育苗技術則於1962年取得成功。
1978年3月,樟子松沙荒造林技術獲首屆全國科學大會獎,同年11月,“三北”工程正式啟動,這一技術隨之推廣應用。
“在彰武,老一輩邁出了樟子松引種造林從0到1的關鍵一步。”黨宏忠讚嘆,“這是件偉大的事情。”
為什麼是在彰武?
彰武,地處遼寧西北部,內蒙古南行的要衝,東北入關的咽喉,素有“全遼管鑰”之稱。它一頭挑着新中國最早的能源基地阜新,一頭連着東北的心臟瀋陽,位居東北亞經濟圈腹地,其東南距瀋陽僅90余公里。
彰武身後的科爾沁,歷史上曾是水草豐美、牛羊肥壯的大草原,由於濫墾過牧、氣候變化等原因,生態系統嚴重失衡,最終演變成中國最大的沙地之一,也成為京津冀風沙的主要源頭之一。其分佈區面積6.63萬平方公里,其中沙地面積3.51萬平方公里,有“八&&瀚海”之稱。
曾經有人計算過,從彰武開車到北京,最少得8個多小時,但如果風力足夠大,這裡的沙塵飛到北京,會比車跑得更快。
據歷史資料記載,新中國成立初期,彰武的自然條件非常惡劣,一年365天中有240多天黃沙漫天,土地沙化面積曾高達96%,糧食畝産不足百斤。風沙以每年5—12米的速度往南推進,直逼瀋陽。
要擋住科爾沁的茫茫風沙,固沙造林成為當務之急。在極度困境中,依靠科學引領,彰武逢山開路、遇水搭橋,成為新中國科學治沙的起點,被載入中國治沙史冊。
科研聚集地
2024年3月中旬,彰武迎來了一批重要客人——中國林科院彰武科技特派隊。
彰武科技特派隊組建於2023年12月,是“三北”工程三大標誌性戰役打響之後,中國林科院瞄準三大戰區的生態治理難點、堵點,聚焦重大科技需求,舉全院之力組建的15支科技特派隊之一。中國林科院分黨組書記葉智、院長儲富祥等院所中心領導兼任各特派隊負責人。
彰武科技特派隊共34名成員,其中14名擁有高級職稱,中國林科院資源信息研究所所長王宏擔任負責人。
王宏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特派隊之名帶來了強烈的使命感,突出了任務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也凸顯了隊伍的專門性和靈活性。
3月,王宏帶領8名特派隊成員在彰武進行了實地調研,足跡覆蓋章古&樟子松苗木繁育基地、萬畝人工治沙示範區、科爾沁沙地南部山水林田湖草沙綜合治理示範區等14個點位,並和當地政府部門、科研機構進行了深入交流。
目前,雙方已就特派隊為彰武縣提供戰略諮詢、政策服務、技術支持、培訓交流四方面的支持和深度合作達成共識,暫定推進2個項目、3個行動。
“任務艱巨。”王宏&&,“我們將全力以赴。”
遼寧省沙地治理與利用研究所(以下簡稱為“遼寧省沙地所”)副所長張學利是和王宏當面交流的本地專家之一,他自1993年畢業後進入遼寧省沙地所工作,至今已31年。
“彰武治沙的最大亮點,是各科研機構交流合作密切、科研成果轉化迅速。”張學利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遼寧省沙地所的前身,是1952年成立的遼西省林業試驗站,現在章古&擁有面積約4.5萬畝的科研基地。國家林草局、農業農村部、三北局、遼寧省科技廳等政府部門,以及中國科學院、中國林科院、瀋陽農業大學、遼寧省農科院等科研單位均在該基地設有相關科研&&或項目。
20世紀80年代,遼寧省沙地所將樟子松育苗技術無償傳授給當地群眾,使得章古&逐漸發展為全國最大的樟子松種苗繁育和集散地,以樟子松為主的特色苗木産業成為當地支柱産業。
據公開報道,章古&鎮現有3600戶農民,85%以上從事樟子松育苗工作,全鎮育苗面積達1萬畝,年産各類苗木約20億株,年産值達9億元,人均苗木收入超2萬元。
2024年5月31日,地處科爾沁沙地南緣,作為“三北”防護林體系一部分的遼寧省彰武縣章古&林場護林員李東魁查看松樹生長情況(楊青/攝)
張學利和王宏是新朋友,和黨宏忠則是老朋友,雙方團隊多年來交流合作頗為密切。2023年4月,他們共同參與、持續多年的項目獲得了中國林學會“梁希林業科學技術獎”,項目名稱為“樟子松固沙林適應變化環境的水分機制與科學經營技術”。
項目起因是20世紀90年代後,“55秋”林持續發生大面積衰退、死亡現象,同時章古&地下水位下降嚴重,引發人們對樟子松這一樹種是否為“抽水機”、是否應換其他樹種造林固沙的焦慮和疑慮。相關爭論持續了十餘年。
樹種問題一旦誤判,將給彰武、“三北”地區乃至全國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
黨宏忠介紹,項目組經過長期、大樣本量的樹榦液流觀測試驗,以及對樟子松根係分佈特徵的挖掘試驗,結合對地下水位的長期監測,得出判斷:樟子松不是“抽水機”。包括該結論在內的國內多項科研成果,為“蒙冤”的樟子松正了名,為國家進一步推廣樟子松固沙造林提供了重要科學依據。
 2024年4月10日,遼寧省沙地所專家韓輝(左)、劉國強(右)在彰武縣章古&鎮調查樟子松根係分佈情況(黨宏忠/攝)
2024年4月10日,遼寧省沙地所專家韓輝(左)、劉國強(右)在彰武縣章古&鎮調查樟子松根係分佈情況(黨宏忠/攝)
推進系統治理
2023年8月3日,彰武縣嘉賓雲集。國家林草局在此召開科爾沁、渾善達克沙地殲滅戰片區推進會,標誌着科爾沁、渾善達克兩大沙地殲滅戰正式啟動。
“殲滅戰打響後,我最深的感觸是,政府對治沙的重視明顯提高,節奏明顯加快。”張學利&&,“非常強調系統治理思維。”
張學利曾兩次參加《彰武縣科爾沁沙地殲滅戰行動方案(2023-2030)》的論證會議,對初稿方案中三大片區的名稱提出修改意見,得到採納。
目前,張學利主持的“沙地人工林提質增效技術”相關課題正在緊鑼密鼓推進之中,課題試驗區亦落在彰武。“如果説20年前治沙,森林覆蓋率的增加值是最受重視的指標,那麼現在,‘高質量’最受重視。”
對於彰武未來治沙之路,張學利建議:一是應更重視將生態建設和農牧民增收結合;二是應適當利用本地鄉土樹種,提高系統多樣性和穩定性。
黨宏忠則強調,要銘記流沙變森林之不易,持續加強樟子松林的經營問題。
32歲的路偉偉是中國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的年輕女學者,2021年,其職業生涯中主持的第一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落子彰武。
“我的研究課題是樟子松林的退化機制——它到底是餓了?渴了?還是生病了?背後的機理是什麼?——為樟子松林的經營提供科學支撐。”路偉偉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公開數據顯示,彰武治沙成績斐然:全縣沙化土地佔比已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96%降至36.56%,森林覆蓋率由2.9%增加到31.47%,揚沙天氣已由1953年的43天減少到近10年的平均5天。遼寧防沙治沙的第一道防線向科爾沁沙地腹地北移了13公里。
當前,彰武正聚焦現存近200萬畝沙化土地,全力推進10項治理任務、56個治理項目,確保在2028年提前完成殲滅戰任務。
在章古&鎮科研基地內,一塊“大漠風流”石碑引人無限遐想。
石碑是1988年彰武縣38萬人民所立,表達對彰武幾代科研工作者接續奮鬥防沙治沙、創造幸福家園的崇敬感恩之情。碑後刻詩云:“八百瀚海首,苦戰卅六秋。足跡遍塞外,智慧獻沙丘;幾程坎坷路,幾番風雨稠。丹心照日月,偉業青史留;綠了章古&,白了少年頭。香飄荒沙灘,譽滿五大洲;千古傳功德,大漠顯風流。”
七十余載時光,從沙進人退到人進沙退、綠進沙退,遼西小城彰武以松為筆,書寫了一段大漠風流的傳奇。如今,傳奇仍在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