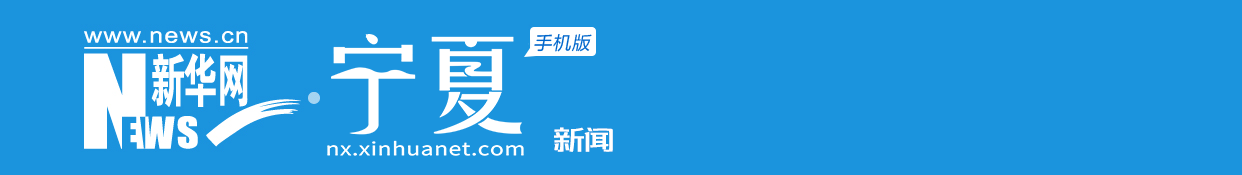20年前的那個冬天,聽説以後都不讓把羊往山上趕了,只能在家裏圈養,從小揮着羊鞭上山的牧羊人田糧和媳婦張巧蘭對坐著生悶氣。
20年後,65歲的田糧走進儲藏草料的屋子,拿出過去放羊的舊把式和那件陪着他走過多年風雨的破棉衣,拍了拍棉衣上的塵土,看著家門口漫山的蔥綠、遠處的草原、圈舍裏的1800多只灘羊,一切仿佛走了很遠,又從未走遠。
20年前,王建紅騎着摩托車從鄉里回縣上,經常會被風沙吹迷了眼。記不清多少次,一個人推着車艱難行走在風沙裏。看到荒草萋萋的沙漠邊緣出現野生的沙蒿、老瓜頭、苦豆子等,有林業專長的王建紅知道,這些植被是草原生態退化的標誌。
20年後,王建紅喜歡開着車到鹽池縣城外轉悠。“到處都是天然氧吧,走近這些樹、這些草、這些無名的野花,有一種説不出來的親近感,每一棵樹都像是我們的孩子,我是看著這一片片林子長起來的。”
時光走遠處,滄海桑田間。20年,迭代了人與風景,縈繞在一代人心頭的貧瘠和蒼涼漸行漸遠,曾經赤地千里的荒漠已是綠野茫茫、草木蔥蘢。回望從枯黃到濃綠的變遷,無數人心潮澎湃,感慨萬千。
(一)
沿着蜿蜒的公路深入草原腹地,鹽池縣王樂井鄉牛記圈村的田糧是這片草原上的牧羊人。
1973年,15歲的田糧從父親手裏接過牧羊鞭,開始了一生的牧羊事業。“起初是給生産隊放羊,隊上有300多只羊,我一個人放。包産到戶後,家裏分到了20多只,慢慢養到100多只。”

站在鹽池縣城北面的山坡上放眼望去,生態長廊鬱鬱蔥蔥,煥發着生機。

空中俯瞰鹽池縣王樂井鄉牛記圈村,曾經的荒漠已是綠野茫茫。
歲月如刀斧在田糧臉上刻出深深印痕,回憶往事的時候,田糧感慨那些年風餐露宿,一個人孤獨地在路上,用雙腳丈量草原的遼闊。“戴個草帽、背個水壺、揣上一塊幹饃饃,一走就是一天。過去鹽池水草好,隨便到哪放羊,羊都能吃飽。羊也有靈性,天黑了,記得回家的路,幾百隻也走不差。”
那個年代,鹽池農村幾乎家家養羊。羊是村民的“活存摺”,娃娃上學看病、家裏紅白喜事、開春的種子化肥全靠羊,為了能讓羊上膘,村民根本顧不得草原的休養生息。每年開春,牧羊人揮舞長鞭驅趕羊群進入草原、山峁,日出離家,日落方歸。
隨着大面積放牧和濫採亂挖,鹽池的生態環境愈發脆弱、植被遭到破壞。“春草剛冒出頭,正是嫩的時候,羊咬不上,便用蹄子刨松後連根拔起。成千上萬隻羊走過後,草原上留下一道道溝壕。”後來甘草價格漲起來,村裏的老老少少開始挖甘草。田糧説:“等於是把土地翻了一遍,把草根挖斷了。人在世上,啥東西都有個數,地上沒了草,沙子就越‘鬧’越兇。”
草原從斑駁嶙峋到赤地千里,羸弱的生態回贈牧民的,只能是羸弱的光陰。2002年,村裏人均收入不足500元,掙紮在貧困線上的村民似乎有解不完的難題。
2002年11月,鹽池縣在全區率先實施封山禁牧,86萬隻羊一夜之間被全部“禁足”。
2003年5月1日,寧夏在全國率先實施全境禁牧,全區近300萬隻羊走下山坡,實施圈養。
關閉了天然草場的大門,牧羊人放下了羊鞭,沿襲千年的“信天游”停止了歌唱。曾經無償、掠奪式使用草原的人們改變了傳統生活方式,開始種植牧草,發展圈舍養殖。
此去經年。
40歲的田增福是田糧的大兒子,成年後一直跟着父親養羊。2012年,田增福和幾個兄弟成立了鴻福祥灘羊養殖合作社,開始了規模化養殖之路,從最初的300隻到現在的1800隻,一年出欄超過千隻,是十里八鄉響噹噹的“羊狀元”。
“我爸有一袋子證書呢。”田增福11歲的小兒子田垣説着,從屋子裏翻出一個大袋子,一個個打開鋪在地上,紅色的證書連綴成耀眼的一片,寫滿“行行出狀元”的樸素真理。田增福説:“上學的時候沒得過一張獎狀,沒想到養羊得了這麼多證書。”
爺孫三代走進圈舍裏,一群灘羊圍着他們“咩咩”地叫,田增福順手拉過來一隻,給我們講述灘羊的營養價值、如何辨認,“前年央視《舌尖上的中國》欄目組來我家取景,就在家裏吃的清燉羊肉,俺們鹽池的灘羊肉質鮮嫩,絕不腥膻,有一股子特別的香味。”“你來看,鹽池灘羊很特別,羊毛都是九道彎,好認得很。”圈舍外,停着一輛轎車和一輛嶄新的挖掘機,挖掘機是田增福剛剛入手的“新傢伙”,除了自養自販灘羊,他還負責收販羊糞,“我喜歡養羊,幹這個行當穩定自在,效益也不錯。”
從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傳統牧歌”到規模化養殖的“新時代牧歌”,人與自然的相處模式在迭代更新。草原也回到自己的青春歲月,吐故納新、暢快呼吸。
(二)
距離鹽池縣城10公里,有一片很小的沙地,沙地中間是一座佇立千年的烽火&。高空俯瞰,這片沙地宛若綠色翡翠中一隻蒼涼的“眼睛”。
鹽池縣林業技術推廣服務中心主任王建紅帶我們穿過一片綠色,走進這片小小的沙地。“從2011年開始,我們以縣城為圓心打造50平方公里生態綠廊,南北5公里、東西10公里。包括公路兩側、國省道全線綠化,路鋪到哪,綠就跟進到哪。現在鹽池周邊的草原又恢復了昔日的風貌。”順着王建紅手指的方向,曾經的沙地穿上了一件巨大的綠色紗裙,密密匝匝的針腳編織,牢牢“鎖”住沙海浪子四海漂流的“野心”。
鹽池縣位居毛烏素沙漠南緣,是寧夏國土面積最大的縣區。20世紀70年代,受三條沙帶包圍,鹽池縣域的輪廓曾經是黃沙蜿蜒。
1995年,王建紅從寧夏農學院畢業後回到家鄉鹽池。剛畢業那幾年在鄉上工作,每到春季就會刮“大黃風”,風一吹黃沙漫天,暗無天日,莊稼、公路被沙土掩埋的情況時有發生,屋瓦院墻被掀倒、柴草垛被掀翻更是家常便飯。
禁牧是依靠封育喚醒自然之力,生態的欠賬和破壞仍然需要人工之力“修補”。鹽池全縣上下總動員,補種曾經消失的綠色,穩住瀕臨流失的水土。在流沙地上扎麥草方格固沙,利用雨季天然降水,在固定的格內點播花棒、楊柴等耐旱沙生灌木,適地選栽檸條、沙柳等苗木,夏、秋兩季重復補植補播,以人工之力喚醒自然之力,形成了跨區域、跨地界治理,全境覆蓋、喬灌草相互搭配的荒漠化治理模式。
身邊的林子慢慢長成,王建紅髮現呱呱雞、狐狸、兔子多了起來,植物種類也有變化,樟子松、國槐、檸條等高大喬木遮蔽的地方,冰草、白草、長茅草、胡枝子等優質草木越來越多,這些是草原生態進化的標誌,還有很多植被是天然生長起來的,體現了草原自然修復的能力。
“以前山是山,水是水,現在山水既有生態效益,也有經濟效益。”鹽池縣委工作人員李相峻説,依託山水打造生態旅游區、防沙治沙園區、旅游觀光帶等生態旅游景點,培育鄉村休閒、農家體驗等特色旅游産品,生態旅游已成為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
經過多年的人工治理和封山禁牧,遼闊的土地經歷着由黃到綠的神奇轉換,鬱鬱蔥蔥的樹林回來了,墨綠濃稠的顏色回來了,潺潺流水和呦呦鳥鳴回來了,那是牧羊人田糧記憶中的草原,是林業人王建紅呼喚的草原。
從荒涼瀚海到無邊綠野,腳下的“一眼沙漠”和眼前的萬丈草原形成鮮明對比。王建紅説:“這一小塊沙地,是我們特地保留下來的,希望後來者能夠記住生態的罪與罰,記住這一堂生動的生態教育課。”
(三)
過去,寧夏的汽車駕駛員從銀川走固原,一路上會經歷強烈的視覺差:從起點的江南水鄉到中途的不毛之地再到終點的高原綠島,“走到哪兒不用看地名,看車窗外的山水就知道了。”
最近幾年,這種“視覺差”在逐漸彌合,基本是一腳油門、一綠到底。從南到北,既有天然林的沉澱厚重,也有人工林搖曳生姿。淺淺綠、深深綠,參差錯落,真正應和了那首古詩“便覺眼前生意滿,東風吹水綠參差。”
播綠不止、追夢不止,這片土地有多少種綠色,就有多少執着地跟黃沙“掰手腕”的治沙人。
他們有着近乎相同的特徵:一樣黝黑髮亮的皮膚、一樣粗糙結繭的手掌,以及相似的性格特質:脾氣倔、韌勁足。從這些治沙人身上,也能讀懂寧夏堅持數十年荒漠化治理背後的汗水與付出。
這些治沙人,就生活在沙漠中,如同沙窩裏一株芨芨草,給點水分就能活,見到落雨就燦爛;如同根係深埋的沙生植物,在沙海之下手足相牽、連綴起條條根脈,沙海之上綠染山河。皓首半生、用汗水澆灌出一片綠洲的“人民楷模”王有德;30多年鍥而不捨、換來沙海泛綠的唐希明;將“一棵樹”種成“一片海”的“全國勞模”白春蘭;帶領全村戰勝“沙霸”的村黨支部書記劉佔有,還有無數沒有留下名字的人們……每個人都是不屈不撓的戰士,每個人都訴説着一代人對綠色的無限渴望。
從濫墾濫牧到封山禁牧,從黃沙蔽日到碧草藍天,幾十年的矢志不渝,寧夏走出了一條西北地區荒漠化治理的生態之路。今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加強荒漠化綜合防治和推進“三北”等重點生態工程建設座談會上,發出“努力創造新時代中國防沙治沙新奇蹟”的時代號召。近年來,寧夏大力實施防沙治沙工程,推進“三山”生態保護修復,全區荒漠化面積減少了231萬畝,荒漠化綜合治理的攻堅戰還在持續。
從“防沙治沙”到“植綠護綠”,生態的變遷是一座豐碑,深深銘記過去、現在和未來,銘記淚水與汗水,銘記舊貌與新顏;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歷史和現實的縱橫交錯,並以自身的實踐證明,給自然以敬意就會獲得公平的回報;是一扇窗口,從這扇窗望進去,看到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環境更美好的家園,看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美麗新寧夏的壯美前景。
朝陽初升,把一片詩意般的祥和灑落在草原之上。陽光下,枯與榮深情對白:我是你的曾經,而你,是我的永恒……(全媒體記者 李東梅 李 濤 何婉蓉 石琪慧 文/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