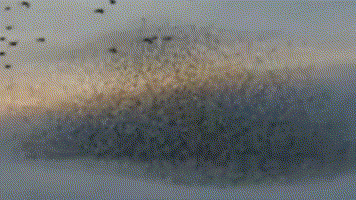英國文學評論家亨利·希金斯最近出了一本新書《如何讀懂經典》,被很多人標記為“想讀”。據説這並非一本新書,五年前初次面世時它的中文名字叫《真的不用讀完一本書》。作者很勤奮,背了不少書,找了不少資料,講解也深入淺出,試圖一步步領著那些沒什麼原著閱讀經驗的人迅速理解一部作品。而作為讀書人,我是古舊派,這樣的做法與殺雞取卵又有何異?可能還不如管中窺豹,一斑都得不到。
首先,這“不用讀完”和“如何讀懂”兩個短語給人的暗示性太過明顯,説白了便是偷懶加成功模式。走捷徑,誰不願意? 但其實讀經典與成功沒多大關係。文學和功利原本就是水火不容的。成功學既已迅速裹挾了當下,為什麼還不願放過孤寡慣了的文學經典呢?用一種與其全然相反的價值去駕馭文學作品,這比將之棄而不顧更為殘忍。
且並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讀了經典就會更成功,應試倒還比較靠譜,能離成功或許更近。然而我粗觀此書對作品的解析方法,倒與中學生閱讀理解的解題思路頗為相似。在最快時間內把握文章主旨,圈出重點段落詞句,分析作者情感,再了解下寫作背景,如此簡單粗暴應付考試尚能讓人原諒,畢竟拿了好分數是奔著成功而去的;可拿來對付文學作品,實在無利可圖又毫無美感,何苦?
當然,並不是説文學作品就應該像天外飛仙一樣虛無縹緲,毫無把握的可能,相反,越是經典的文學作品它的存在感便越強,對現實的介入和幹擾也會越強。帶著思考,理解,乃至參悟的願望走近一個作品,不但可行而且必要。然而我們必須明白,文學寫作,與哲學、歷史,或其他人文科學類寫作最大的區別即在于,它的寫作過程、寫作成果和最初的寫作目的往往不完全是一致的,即便作者是帶著一加一等于二的明確目標去構思作品,在文本完成之後,也沒有任何人敢保證它的結果就是“二”。托爾斯泰構思 《安娜·卡列寧娜》時對這位女主人公帶著明確的批判性,可當這個人物出現在他的手稿中時,慢慢地這批判的目的被一種更復雜的內心驅動力所擾亂了。最終,安娜成了文學史上非常難以用任何既定的觀念去下定義的一個人物,一個非常有魅力的女性形象,這就是文學寫作的特殊。
寫作的特殊性同時在左右閱讀的特殊性。曾有人問我閱讀文學作品與閱讀其他類型的作品最大的區別在哪裏。深思後答:在于語言。過于追求對內容的了解、主題的把握、人物的解析,乃至背景知識的掌握,這種做法對作品最大的傷害在于它們都忽略了文學語言的存在,以及它在文學作品中所佔據的根本性地位。讀作品,始于語言,歸于語言。語言既是載體,又是媒介,更是入口。絕大部分作品的精氣神是由語言來呈現的,而不僅僅是敘事。更準確地説,敘事亦不可與語言割裂開來看,否則作品就會失去獨特性。無論是丹麥王子哈姆萊特,還是 《紅與黑》 中的于連,也許我們尚可沿著結構主義的思路去歸納出一些故事情節的必然性,然而人物的獨特性,情感的獨特性,卻是怎麼也無法分門別類的。越經典的文學作品,越難以被歸類,或者勉強歸類,如什麼歷史小説,家族小説,復仇小説,倫理小説等,也只會讓讀者覺得成色減去大半,有興味全無之感。所以,帶著理性的願望去窺探一部文學作品固然好,卻是不夠的。條分縷析固然可以幫助理解,卻到底是有所欠缺的,因為文學作品是精神性的産物,其思想層面上的意義雖然重要卻不是終極的意義。而要接近某種精神的內質,在文學作品內,非通過語言不可。
語言是讀者在閱讀中與作者發生共鳴,産生共情的基礎,也是唯一的通道。感性地説,跟著作者所寫的字一個一個去讀,你憑借皮膚或嗅覺就能接觸到這字後的喜悅與悲傷,而這是無法通過整體把握和條分縷析去做到的。所以我更願意把閱讀的過程形容成是去軋一條馬路,而不是開一輛車駛向目的地。文學作品的結局絕不是目的地,讀沒讀完,讀沒讀懂,也同樣不是。閱讀本身是一種無始無終的行為,因此,它才能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看待世界的方式。當然,作為多種方式中的一種,我堅持文學閱讀不宜被神聖化,正如它不宜被功利化。往往正是神聖化的傾向導致了功利化的行為,而這,實在不是文學在當下應有的位置。我更相信,與文學作品相遇不過是一段可遇而不可求的緣分。(陳嫣婧)

-
學校只剩一名學生,她卻堅守了18年
2018-03-01 14:40:53
-
有重大變動!騎共用單車的一定要注意了
2018-03-01 14:40:53
-
2018年,樓市會有哪些新變化?
2018-03-01 09:01:20
-
農村小規模學校“尷尬”的根源在哪
2018-03-01 09:01:20
-
曹遠徵:新舊動能轉換的核心是什麼?
2018-03-01 0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