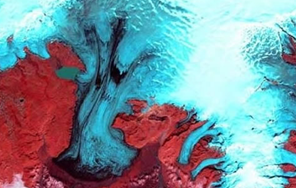5月13日繼續擠兌,人數與12日差不多。為了安定人心,本來星期六半天辦公,上海分行特意延長辦公時間,結果擠兌人數一下子減少了400人;此後周日本來休息,也照常營業半日,結果擠兌人數不到百人。張公權此刻才算舒了一口氣,記下“風潮似已平息”,但是他也沒有十足把握,在目睹13日擠兌情況之下,上海分行行現金也開始減少,究竟能否支撐下去其實未必完全有把握,需聯繫外資銀行給予幫助。
在幾天的擠兌之下,上海分行雖全力應對但也幾乎面臨困境,畢竟擠兌就是一個信心比較的過程,在市場踐踏之中,誰也不知道擠兌什麼時候過去,甚至危機開始退散的時刻是壓力最大的時刻,“滬行庫存有200多萬元現銀準備,擠兌數日共兌出160余萬元,同時商存款項被提取數亦達百萬元”。于是,外資銀行的幫助就顯得分外重要。5月15日,宋漢章經理往訪匯豐銀行和正金銀行兩家外資銀行尋求幫助,諸多外資銀行讚成協助上海分行“至必要限度”,由各外資銀行共同承擔對上海分行的200萬元透支借款。
當時外資銀行信用良好,所以鈔票得到更多認可,庫存現洋頗多,所以上海分行不得不借助其幫助,而外資銀行也需要市場穩定。當時勢力最大的匯豐銀行隱性承擔了維護市場穩定的責任,匯豐銀行貸款額度佔據1/5,為40萬元。此外,當天還決定由華俄道勝銀行“出早倉”(資金一般是下午出庫,早倉表示提前提出)以幫助上海分行。其實上海分行並沒有動用這筆錢,但是市面得知這一消息之後,擠兌風潮旋即散去。
當然,據參與者回憶,雖然宋漢章在外資銀行中頗有聲望,但是交談之中並非單憑信用,提供了上海分行行址及蘇州河沿岸之堆棧、地産道契等為擔保。對比之下,雖然也有呼吁幫助交通銀行的聲音,但是因為交通銀行聲譽一向不如中國銀行,所以外資銀行對兩家中資銀行的態度也是兩樣。
到了5月19日,風潮總算徹底平息,張公權如此記錄戰果,“上海中國銀行之鈔票信用,從此日益昭著。南京、漢口兩分行鑒于上海分行措施之適當,並獲當地官廳之合作,對于發行之鈔票,及所收存款,照常兌付現金。影響所及,浙江、安徽、江西三省,對于中國銀行在當地發行之鈔票,十足使用”。
從經濟上來看,上海分行已經勝利,此刻可謂“家有千金,行止不驚”,在銀行加班加員應對擠兌的努力之下,擠兌風潮散去。不過,經濟只是一方面,此刻又傳來各方面的聲援。5月16日各國駐京公使團向領事館復電,讚同協助上海分行,但張公權當時表示擠兌風波已經平息,上海分行無須外援。
盡管此刻經濟上已經不需要外援,外援的政治含義卻十分清晰,對于日後的追責贏得了空間。而且,上海分行的應對也感染了不少人,原本持中立曖昧態度的機構個人也明確支援上海分行,例如上海總商會即在《申報》表示,“查中國銀行準備現金甚為充足,不特發行之鈔票照常兌現,即將來存款到期亦一律照付。該滬行內容之可靠、誠信而有證,惟鈔票為輔助現金,全賴市面流通,斯金融不致窒塞。該滬行既備足現金、兌付以保信用,而各業商號自應一律照收”。如此趨勢之下,等到袁世凱在1916年6月6日去世之後,根據李思浩回憶,執政的段祺瑞對于上海分行停兌的態度改變為“非常和緩”,承認停兌是勉強應急策略,而上海分行在租界之內,“與外國商人關係較深,停兌不易辦到”。
袁世凱去世之後,大局已定,停兌風潮也意味著上海分行的完全勝利。至于“停兌令”的始作俑者梁士詒,在袁世凱去世之後被繼任總統黎元洪下令通緝,繼而逃亡海外,日後在一切風平浪靜之後鹹魚翻身,再度卷土重來,重新入主交通銀行,借助西園借款盤活交通銀行——這就是鬧哄哄的民國政治。
這次京鈔擠兌事件之後,1921年又重演過一次。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從1916年到1923年整理京鈔,在戰亂中歷經幾個階段才算基本完成。中國銀行也在這一過程中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銀行。1926年,中國銀行吸納的存款總額達到32 848萬元,發行鈔票13742萬元,分別佔25家重要華商銀行存款總額和發行總額的35.1%和60%。
這一次勝利雖然是在張公權等人運籌帷幄之下展開,但是其中的成功也依賴于當時的政治經濟大背景。
首先,不得不承認北洋政府是一個弱勢政府,這反而意味著它不會擠兌得非常霸道,北洋政府時期其實也是一個相對溫和的時期。正因如此,“停兌令”的執行並不是十分嚴格,南方對北洋政府的做法也表示異議,“北京政府宣布此舉,係欲使中交紙幣跌價,造成獨立各省經濟上的恐慌,北京則可席卷現金,以發軍餉”。如此氛圍也給予張公權等人抗命的空間。這其實是權力分散之下“東南自保”在金融領域的體現,即使秋後算賬,在各界的抗爭斡旋之中,最終也不了了之。
其次,這看起來是張公權的勝利,其實更是江浙財閥乃至工商界的勝利,也是市場力量的勝利。張公權最為倚重的其實是股東和工商界人士的力量。他依托于張謇、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蔣抑卮、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銘、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等人,借助股東力量公告天下,“環顧全國分行之最重要者,莫如上海一埠,上海為全國金融樞紐,且為中外觀瞻所係,故以為保住中國銀行必先自上海分行始。中國銀行滬行決定由股東會竭力維持,將來各業企業如有損失,均由股東聯合會負責向政府交涉”。
換言之,此役的勝利依賴于中國銀行商股身份的強大。這也是北洋時期的一大特點,因為北洋政府財力積弱,所以官股也少,稀釋之下銀行內商股的比重增大,而且話語權不少,參股人員也不再類似晚清更多是官商身份,而是以商業為主。對中國銀行而言,1915年大部分為官股,但是之後商股比重開始增加,1917年從17.01%升為59.29%,1921年為72.64%,1923年猛增到97.47%。根據曾擔任中國銀行總裁的馮耿光的回憶,中國銀行幾位首腦雖然性格不同,但都想把中國銀行辦好,也認識到要維持它的相對獨立性就要盡量擴大商股權益、削弱官股力量,以免受到政局變動的影響,“北洋政府財政部因為需款應用,經常將該部持有的中國銀行股票抵借款項,我們就慫恿他們陸續讓售給商業銀行,到北伐前夕,官股為數極少,只剩5萬元了”。
最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人員地位也不可不提。當時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總行都在北京,但是兩行在上海都設有分行,而且地位重要,其重要性不僅在于上海金融市場的中心地位,更在于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半數準備金都屬于兩家的上海分行。根據張公權回憶,“當時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發行之兌換券計七千余萬元,現金準備約兩千三百余萬元。內中:中國銀行存有現銀三百五十萬兩,銀幣四百八十八萬;交通銀行存有現銀六百萬兩,銀幣五百四十萬元。此項現金準備之半數,屬于上海中國、交通兩分行”。
對比之下,交通銀行的歷史本身與中國銀行不同。北洋政府對于交通銀行成為國家銀行頗有助力,而袁世凱的親信梁士詒在交通銀行地位不凡,從交通銀行幫辦到最終擔任交通銀行總理。交通銀行初創之時雖然獲得輪、路、郵、電四項存款往來,但是在歷年墊資與經營不善之下甚至虧損280萬兩以上,“行務停滯,幾有不能支援之勢”。梁士詒謀求袁世凱支援,擴大交通銀行權力,為交通銀行謀取到國家銀行權力之後,交通銀行一直在他控制之下,交通銀行的經營狀況卻不如中國銀行。當時上海《新聞報》刊登了一則“北京特別通訊”,據説: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兩總行在停止兌現、付現的院令發表前,曾致電向各地分行徵詢意見,交通銀行分行均無意見,而中國銀行各分行都不讚同,甚至有言“交通銀行自殺,係屬自取,中國銀行陪殺,于心難安。寧可刑戳及身,不忍茍且從命”。
從全國來看,因為地域風格有異,各地對“停兌令”的執行力度和步伐也不一樣。多數地區遵照實行,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堅決抵制也有其特殊性。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地位特殊,辛亥革命爆發後銀行停業清理,然而大清銀行中除了官方股份,也有商股。在商業股東出面斡旋之下,南京臨時政府同意中國銀行于1912年在上海(原大清銀行的舊址)開業,次年才設總行于北京,固定股本總額為銀元6 000萬元,官商各半,由此可見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的地位在中國銀行內外都不低。至于交通銀行上海分行,其主管是交通係官員,到任時間不長,更是與商人及銀行業務不熟,外資銀行對于他們的態度也不同,所以不得不對“擠兌令”遵照執行。而經過這一次,交通銀行上海分行的結局與中國銀行上海分行更是不同,時隔一年之後才重新營業,其總行也差點遭遇撤銷。
經過這一次風波,張公權一戰成名,可謂在金融界揚名立萬,而且在政界與新聞界也獲得不少擁護,後來梁啟超邀請他擔任中國銀行副總裁,花費數年整頓京津地區的京鈔問題,這為他日後作為江浙財閥代表支援蔣介石奠定了基礎。
對抗擠兌成功不僅僅是張公權一人的功勞。據了解內情者評價,張公權交際活絡,與江浙銀行家、政界以及新聞界多有聯繫,從政經歷使得他對外處理事務得力。對內而言,宋漢章在行內有實權,對外資銀行有信用,而當時上海分行襄理胡氏在錢莊有地位,正是他疏通中國銀行到上海錢莊市場交易,使得錢莊給予中國銀行的地位是同業而不是普通客戶。由于三人在不同方面“各有所長,相得益彰”,促成了中國銀行在這次風潮中屹立不倒。
至于宋漢章,雖然一直以來被談到的頻率低于張公權,其實他對于中國銀行的貢獻也很大,其服務時間更久,資歷更高。他經歷了清朝、北洋、國民政府等不同朝代的中國銀行。張公權説起宋漢章,評價是“靜默寡言,但是朝夕相處得益亦多,美德有自奉簡樸、操作勤勞、辦事認真、愛惜公物、公私分明”。宋漢章日後擔任中國銀行總經理,1946年任四聯總處理事。在孔祥熙辭職的情況下,年近80歲的宋漢章還在1948年4月任中國銀行董事長,目的也是為了保持中國銀行獨立。1949年他辭職去巴西,1968年在香港去世,享年96歲。宋漢章的一生,除了這次對抗北洋政府,還曾經對軍閥陳其美、蔣介石的借款要求強硬回應,有人甚至將他稱為中國銀行的精神領袖。至于胡氏,曾有上海錢莊經歷,張公權説他對于錢莊歷史業務尤其熟悉,與之談論市面情況增加知識不少。
在“抗兌令”中,中國銀行股東聯合會在致電國務院、財政部和中國銀行總行的電報中提到,“次中央院令,停止中、交兩行兌現付存,無異宣告政府破産,銀行倒閉,直接間接宰割天下同胞,喪盡國家元氣,自此之後,財政信用一劫不復。滬上中國銀行由股東決議,通知經理照舊兌鈔付存,不能遵照院令辦理,千萬合力主持,飭中行遵辦,為國家維持一分元氣,為人民留一線生機,幸甚”。日後發展也多少印證這些銀行家的當年期待,雖然政局變動,中國銀行仍舊得到長足發展,中國銀行存款總數1917年年底為1.4億元,1928年年底為3.8億元;鈔票發行額1917年年底為7 000萬元,1928年年底為1.7億元。1928年年底,全國銀行發行總數為2.9億元,中國銀行發行總數約佔一半;全國各銀行活期、定期存款總數為9.8億元,中國銀行存款總數約佔4成。中國銀行的地位不僅在全國卓越,在上海等地甚至高于官方的中央銀行,“1934年年底,全行存款總數達5億余元,各項放款為4億余元,均較中央銀行多一倍許,發行總數為2億余元,較中央銀行多兩倍半”a。
“京鈔風潮”與“抗兌令”背後,不僅折射出中國銀行業與銀行家轉瞬即逝的黃金時代,也暗示了一個教訓:政府無信用情況下,民眾往往更偏好白銀之類的金屬貨幣,金屬貨幣的存在其實天然對于紙幣的通脹是一個束縛,若非如此,不受控制地發行紙幣必然引起通脹,引發金融動蕩。可惜這一教訓並不被後來的國民政府所接受,在白銀退出歷史舞臺之後,紙幣的效應被放大再放大,民國政府在通脹的道路上一路狂奔,直至滅亡。

-
 前11個月 河北國企利潤同比增長83河北國企利潤同比增長83.2%科技人工智慧2016-12-24 12
前11個月 河北國企利潤同比增長83河北國企利潤同比增長83.2%科技人工智慧2016-12-24 12 -
前11個科技人工智慧2016-12-24 12
-
前11個月 河北國企利潤同比增長83河北國企利潤同比增長83河北國企利潤同比增長83河北國企利潤同比增長83.2%科技人工智慧2016-12-24 12
-
2017年“我向總理説句話”建言徵集活動
2017-02-21 09:55:26
-
“國家賬本”邀您過目,哪筆花銷你最關注?
2017-03-06 13:49:56
-
[兩會單車日記]一輛有故事的共用單車
2017-03-06 13:49:35
-
扶貧攻堅,你有哪些錦囊妙計?
2017-03-09 10:56:21
-
古往今來幾時“休”:看中國“休假制度”變遷
2017-03-09 10:5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