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笛響徹江面,船下洪浪滾滾。清晨六點,李忠元終於登上了當天開往江新洲最早的一趟輪渡。
過去的一整夜,他驅車800多公里從福建泉州趕回家鄉江西省九江市,只為早一刻踏上江新洲堤壩,身旁還有更多聞“汛”而歸的同鄉。
6月下旬以來,中國南方多地遭遇洪澇災害。受強降雨和上游來水影響,長江水位持續上漲。地處江西、湖北和安徽三省交界處的江新洲,在長江江心猶如一葉“孤舟”,四面環水。
“回家,回家,一起抗洪守堤壩”,成為在外工作生活的江州兒女齊刷刷的行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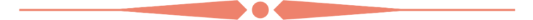
“家書”喚,返鄉抗洪

暴雨如注,雷電交加。江新洲北堤因長時間洪水浸泡和暴雨沖刷,內堤堤腳泥土松軟,存在潰堤危險。2日的漆黑雨夜,60多名村民組成搶險隊,迎着風浪,用碎石加固堤腳,開挖人字形“導滲溝”,讓堤內清水流出,防止險情擴大。
“近半個多月裏,雨下個不停,江水漲得猛。”負責這段堤壩的江洲鎮人武部部長鄭屹説。
受連日強降雨影響,長江中下游幹流洞庭湖入江口以下河段全線超警戒水位,江西北部地區受災人數超百萬,江西省政府已部署專人進行堤防巡邏與救災。

江洲鎮常住人口僅數千人,且多為老人和孩子。
“鄉親們,當您看到這封信時,家鄉需要您。”7月2日晚,當地發出防汛“家書”,號召青壯年游子返鄉抗洪,守衛家園。
當晚,江洲鎮柳洲村55歲村民李忠元在手機上看到“家書”後,當即拉上兒子連夜從福建開車趕回。次日清晨,李忠元在防汛哨所值班人員裏第一個寫下自己的名字。
“得知水勢上漲,就想立馬回來,一刻也等不了。”李忠元説,往年每逢汛期都會回鄉防汛,“這是我們江洲人的傳統”。
越來越多江洲人聞“汛”趕回——
“70後”的劉昌友回來了,歷年每次大汛都參與抗洪,對巡堤除險有着豐富經驗的他,認為必須盡自己一份力;
“00後”的洪嘉樂也回來了,剛結束大三期末考試就從溫州返鄉,正在堤壩上學習怎麼發現滲漏、泡泉等險情;
……
截至7月4日晚,防汛“家書”發布2天內,已有1298名在外村民自發返鄉參與防汛抗洪,共渡難關。

守住堤,就是保住家

江洲鎮後埂村72歲老支書梅俊洲又上堤了。“每到汛期,夜裏兩三點都睡不着,閉上眼睛,眼前都是堤壩。”梅俊洲説。
巡堤查險的竭力盡心,源自對水患的刻骨銘心。
過去,江新洲每逢大汛必罹水患。26年前的一個暴雨之夜,洪水撕開了江新洲大堤,一夜間大片房倒田淹。
這段“破壩”經歷讓老一輩江新洲人不堪回首。洪水漫灌的經歷,讓他們格外重視汛期防護。
每年4月開始,當地就會備好碎石、沙子、編織袋;在環島40多公里堤壩上建起170多座防汛哨所,每村劃分責任區;幹部和群眾肩並肩沿着堤壩呈“丁字形”巡堤查險……
1998年9月,江新洲的安置大棚裏,一個女娃呱呱墜地,父母給她取名“志江”,寓意“志在治江”。
余志江自小暑期記憶,就是和父母一起巡堤查險。四年前她剛大學畢業,便扛起鐵鍬上了大堤。
眼下,她在廣東深圳一家物流公司工作,看到防汛“家書”後就收拾行李,打算返回家鄉盡自己一份力。
“大堤在,家就在,守住堤,保住家。這是我們一代代江新洲人的信念。”余志江説。

升級的堤壩,延伸的防線
2020年,江洲鎮柳洲村村支書洪棉雪因連日堅守堤壩,脖子上被烈日曬出一個黑白分明的“V領”;今年,他負責協調安排返鄉村民上堤,依然忙碌,但多了份淡定。2021年大堤加固硬化後,如果沒有特殊險情,村民防汛都不用下水了。

以往防汛搶險時,難免要下水鋪設防浪布、碼放沙袋,“有的村民每次防汛後,都會患上血吸蟲病”。
而今,走在江新洲北堤,過去洪水沖刷最嚴重的迎江外壩,已用鋼筋混凝土硬化。
相比四年前,記者採訪發現,江新洲堤壩在“生長”,防汛機制在“改善”,手段設施在“豐富”。
無人機巡堤、可拆卸浮橋、大堤防滲層……眾多新設備、新設施都出現在江新洲本輪防汛中。尤其是江新洲堤壩整體加高後,環島大堤防汛哨所從原本每隔200米一個,調整到400米一個,原有171個哨所減少至80個。
“目前防汛壓力有所減輕,但科技手段還無法完全替代人工巡查。”江洲鎮水利建設委員會黨總支書桑培德説,一些隱藏在草叢中的泡泉、泥土松軟等險情,還是要靠“老辦法”巡查才能及時發現。
“如今,江新洲兩道防汛‘堤壩’都升級了。”柴桑區防汛第一指揮部指揮長李三榮説,一道在抵禦洪水,另一道在群眾心裏。
7月4日傍晚,長江九江站出現洪峰超警戒水位1.86米,居有實測記錄以來第7位,江新洲又一次經受住了考驗。水利部長江水利委員會預計,長江中下游各站到7月中下旬才能陸續退出警戒水位。
洪水未退,值守不停。抗洪防汛的奮戰仍在繼續。

監製:衛鐵民、劉暢
記者:黃浩然、李勁峰、周密
編輯:劉暢
新華社對外部
新華社江西分社聯合製作
中國故事工作坊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