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費文化盛行的當下,人與人相識的機會和方式越來越多,互聯網為我們打開了海量選擇之門和速配按鈕。但無論是選擇進入還是持續發展一段情感關係,似乎都門檻高企。更簡單來説,愛一個人正變得越來越困難。
這在法國社會學家伊娃·易洛斯的書中,被稱為“冷親密”:在市場機制和消費文化裹挾下,在技術加持下,我們與人相識的方式越來越多,而愛上一個人,卻變得越來越難,維持一段愛情和婚姻也更不容易。
孤獨、疏離、冷淡的情緒,瀰漫在原子化生活的單身青年群體中。年輕人使用各類線上交友App,多次快速且粗糲地經歷“對方對你無感”“對方認為你不合適,已取消喜歡”“下一個更好”……部分青年陷入“即烹即配”的“預製菜化”擇偶困境,“斷崖式分手”“快餐式愛情”往往相伴隨行。情感交往變成可被評估、量化乃至交易的標準化、流水線作業的實體,原本“熱”的親密關係逐漸趨於冷靜、理性。
“願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屬。”任何時代都有自己的情感聯結方式。冷親密正作為一種新的情感關係配方,催生出如“相親劇本殺”“婚禮主題公交巴士”“婚姻文化公園婚禮”這樣兼具娛樂和婚戀功能的新消費模式,試圖幫助青年樹立安全、健康、信任的親密觀。應當看到,過熱過火與過於冰冷,這兩個極端都非愛情的正確打開方式。現代人更有情緒自控能力和情感邊界意識,但無論如何,要相信愛的本質力量,喚醒情感力,走出愛無力、愛冷漠、愛困難,重塑高質量親密關係。
統籌實施:周清印、鄧伽編輯策劃:鄭雪婧
采寫撰寫:鄧楠、李曉婷、熊嘉藝、張楠楠、張睿、程曉莉
之一:渴望愛,無力愛
半月談記者鄧 楠 李曉婷 熊嘉藝
雖然渴望愛,但可能已部分喪失愛的能力。冷親密指向的便是,人們在內心深處對親密關係和聯結的渴望,同時又本能地排斥、懷疑、擔憂和恐懼。
過去我們常常稱呼伴侶為“愛人”,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會選擇使用“隊友”這個詞來形容伴侶關係,用“打怪升級”這類游戲化的詞詮釋未來的共同生活。用詞方面不見“愛”這個字眼,悄然揭示了一種情感之變。

速效與慢熱
“從軟體上認識,加微信聊天,一週內約見面吃飯。如果一週內沒有進展,基本就默認沒戲,迅速換下一個。”26歲的媛媛這樣描述使用相親交友App的流程。她認為,這種“程式化”會讓人覺得枯燥乏味從而厭倦,身邊使用這類App超過一段時間的朋友不少都放棄了。
“線上不靠譜,95%都不會聊起來,照片一般的就更不想聊了,除非特別好看,我才會主動一點。”28歲的胡先生雖然不看好線上交友,但相比線下熟人介紹,他還是願意將相親陣地放在線上。“線下的話,萬一對方覺得你還可以,但你又覺得不合適,對介紹人需要有一個維護成本,很麻煩。線上不理就不理了,沒有那種所謂的心理壓力。”
“現在大家都比較忙,感覺你對我有興趣,我可能嘗試幾次,如果還是不搭理我,那可能就漸行漸遠了。大家都是‘一對多’,説實話都分不清誰是誰了,肯定不會像過去那樣,再上趕着追求對方,反正還有下一個在等着。”29歲的小黃説。
30歲的白女士選擇只戀愛不結婚。她不想步入婚姻的理由,一方面是缺乏動力。“結婚相當於親密關係的經濟合約,我已得到了親密關係,沒必要再跟這個人深度綁定。”另一方面是受原生家庭的影響。“就算我父母離婚是個正確選擇,我作為孩子也是其中的受益者,但在潛意識裏,就是想把婚姻裏那些東西看得更清楚再想去面對。我知道這不現實,也希望能盡量克服這種恐懼情緒。”
胡先生也&&,年輕人的脫單壓力部分源於父母。“我原來跟爸媽常打電話,現在打得少了,因為他們每次都催,跟我説你哪個同學結婚,哪個同學的孩子結了婚,天天這樣。”
“婚姻感覺就像為了完成父母的任務,結婚然後生小孩。但現在年輕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能過就過,不能過就離。”28歲的小一説。
“慢熱”是受訪對象們提到的高頻詞之一,認為結婚不是一拍腦袋就決定的事,如果雙方在尚不成熟的時候選擇結婚,後面很可能會造成傷害且留下遺憾。“作為獨生子女,雙方也需要在更長的交往中變得更成熟,適應有另一個人的生活,可能也更需要一段時間去達到適婚的心理年齡。”27歲的馬銘説。
“伴侶不是既定的,而是靠時間養成的。無論如何,我都需要一個長期且緩慢的過程來做心理建設,不需要轟轟烈烈的婚姻,順其自然雙向奔赴就很好。”33歲的包女士説。
不少受訪者認為,當下婚育不是一個必選項。“我們這代人更在意的是要怎麼養育孩子,經濟儲備夠不夠,能給孩子什麼樣的教育資源,這才是一種更負責任的觀念。”小黃説。
“育人先育己”是眾多受訪者的共識。“不能只要求孩子考好成績,家長對自己也要有要求,不能雙標。”馬銘説。提起養孩子的“經濟儲備”,他也很“頭大”:“有個同學在杭州做樂器興趣班,一節課(50分鐘)快400元了,有的機構上大課每節4位數,以後如果有小孩根本不敢想怎麼報班。”
馬銘也關注女性求職問題。“我們國家並沒有到一個人隨便打打工就可以養活家庭的程度,如果不能無後顧之憂地生育,女性怎能維持內心的安全感呢?”
已婚的洛依身體條件不好,醫生不建議生育,她自己也正處於事業上升期。“結婚一年還不到,婆婆一聽説我來月經就很生氣,質疑我為什麼還沒有孩子。”由於在社交&&上頻繁搜索婚育相關信息,她經常收到關於“産後傷害”的推送,“我們真的太缺乏這方面專業的護理和心理疏導了”。
“Solo活”、不信任、邊界感
“Solo活”指獨自生活,部分受訪單身青年&&在“一人食”“寵物經濟”等風潮下,一個人過得也挺好。“工作太累了,休息時間只想躺在家裏,加上社恐(指社交恐懼),也比較抗拒有一個人加入我的生活。”網友小一説,“當男方提出進一步交往要求時,我都拒絕了。可能是我單身太久了,感覺一個人的生活很自在。”
“i人(指內向)與e人(指外向)”“j人(指循規蹈矩)與p人(指隨心所欲)”“淡人(指雲淡風輕)與濃人(指濃墨重彩)”……網絡中流行的社交人格是年輕人參考的擇偶標準之一。部分受訪者自認為是“i人”,很難和相反屬性的人兼容。
家裏養3隻貓的月亮説:“感覺身邊的e人朋友找對象很容易,而我是個i人。社會交往太複雜,騙婚騙彩禮案例太多,我只要有自己的貓就足夠了。偶爾生病確實也想要人陪,但如今在網上找個陪診的也挺好。”
受訪青年&&,“網絡情緣一線牽”成功的案例也有,但就像中彩票。30歲的樂樂不信任以相親為名謀利的&&,“感覺忠誠度不靠譜,騙子多,不會認真找對象”。
利用婚戀App詐騙的案件並不鮮見。媛媛雖然不信任這些App,但她覺得在App上像HR(指人力資源)一樣看過很多份“簡歷”後,提高了自己對相親對象的鑒別能力,逐漸明確了自己擇偶的標準,也算有所收穫。
部分受訪者認為,父母不講“邊界感”令他們受傷,加劇了冷親密,甚至産生“斷親”的念頭。
29歲的康康是一名心理諮詢師,她認為很多家庭的父母是“入侵式”的,不尊重孩子的邊界。孩子會以為親密關係就是得讓對方感到快樂,從而犧牲自己,得去討好迎合。“我們沒有得到很好的親密關係示範。這實際上就是一種控制,令人不舒服甚至痛苦。”她坦言,“冷親密時代可能恰恰是一種自我覺醒,年輕人慢慢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或者至少知道不想要什麼樣的親密關係。”
“你結婚了我們的任務就完成了”“你再不結婚這輩子就完啦”“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白女士總結了家長催婚的“經典語錄”,令一些受訪者頗為共鳴。
“不結婚就會被冠上不孝的帽子,每次被催婚就像被掐住脖子。”白女士坦言,“爸媽不能理解,未婚和已婚不是對立的。婚姻之外的互助選項太少了,我們的關係出現了多樣性,但沒有一套新的東西來適應,這就導致無論怎樣,都得裝進婚姻關係的套子裏。事實上,我們這代人追求的是能讓人與人之間真誠地互相扶持,感覺到安全、信任和力量,這才是高質量的親密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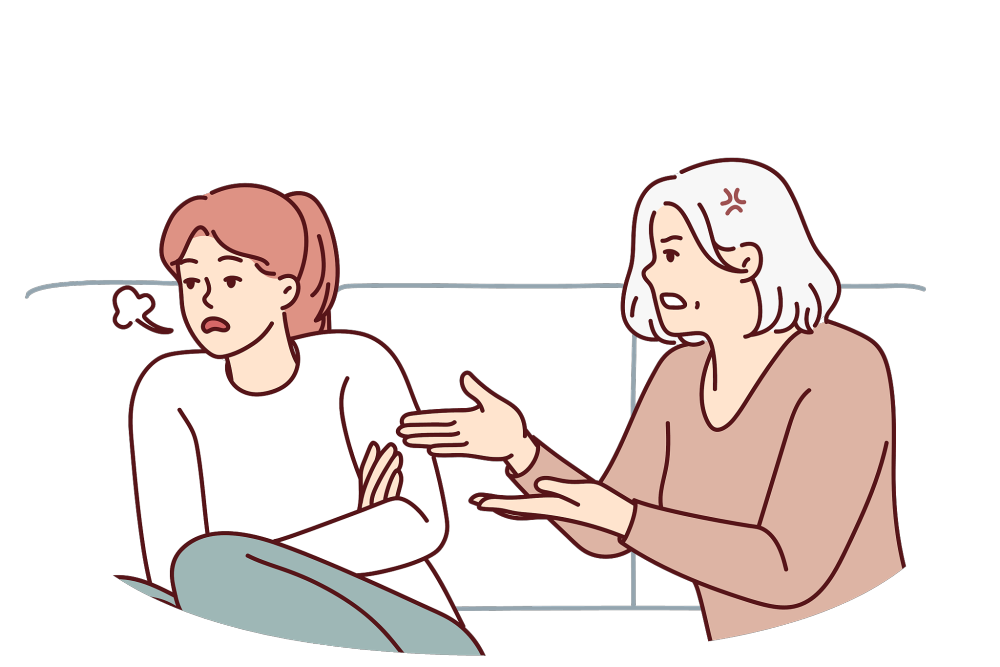
讓親密更安全、健康、滋養
天津大學的“戀愛心理學”課程格外搶手。授課教師王小玲在課程設置方面特別注重學生的參與感和體驗感,設計了很多模擬和實踐環節。比如,針對原生家庭對青年婚戀的影響,她專門佈置了一項課下作業,對自己的父母進行訪談。“後來,許多同學還拉上自己的父母一起來聽課。”王小玲説,這樣的環節設置加深了孩子和父母之間的相互理解。“是否脫單並不是考核學習效果的標準。”王小玲期待,學生通過課堂所學,有能力去愛,也能獲得更多的幸福。
新婚俗受到年輕人歡迎。吉林省長春市南關區民政局與長春公交集團西南汽車公司聯合推出的首款“百年好合—幸福啟航號”主題婚禮巴士,容量大視野好,一輛車可達到多輛轎車的運載量。車輛平時在線路上正常運營,新人租用時改為婚車,充分利用現有城市公交資源,為新人帶來與眾不同的婚禮體驗。
青神是蘇東坡初戀的地方。四川省眉山市青神縣以蘇東坡與王弗“喚魚聯姻”的典故修建喚魚公園,其中婚戀文化成為公園建設主題之一。新人按中國傳統行牽巾禮、拜堂禮、卻扇禮等,一起許下愛國護家、相守一生的莊嚴承諾。
此外,劇本殺是受訪青年認可的相親方式之一。網友小謝説:“比起線上相親App,劇本殺能讓年輕人線下接觸時間久一些,通過面對面游戲,可以大概看出對方的表達能力、邏輯能力、共情能力,而且劇本殺是可以拋開現實身份進行社交的方式,比較放鬆,既能娛樂,還可能結交到新朋友。”她認為,劇本殺等破冰游戲能一定程度緩解初遇的尷尬,“不像那種純聊天相親,兩人不熟‘尬聊’,漸漸就不知該聊啥了”。
全球視域下的冷親密
韓國統計廳發布的數據顯示,韓國2023年登記結婚的新人數量較10年前減少40%。逐漸增多的晚婚和不婚現象已給出生率造成衝擊。據韓聯社報道,近期一項對500名19歲至23歲韓國年輕人的調查顯示,50.4%的調查對象不打算結婚或者生孩子。
韓國最大的婚姻交友&&“DuoInformation”調查顯示,25歲至39歲未婚者普遍認為,丈夫的理想年收入約為6000萬韓元(32萬元人民幣),妻子的理想年收入約為4300萬韓元(23萬元人民幣)。但這與現實相去甚遠。由於經濟壓力大,“是否足夠有錢”成為決定韓國人能否結婚的關鍵因素,甚至超過“性格合適”和“家人認可”等傳統因素。
33歲的車先生最近結束了一段5年的戀情。他曾經和女友考慮結婚,但常因為買房發生爭執。“前女友和我對這段關係失去了信心。”車先生説,“我們年收入大約有6000萬韓元(32萬元人民幣),不足以支付公寓的首付和貸款。無數次因為錢爭吵後,我們已經精疲力竭。”他説,因為錢不夠,生孩子這件事更是想都不敢想。
英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數據顯示,英國成年人中,只有不到半數登記結婚或結為民事伴侶關係。初次登記結婚的英國人年齡越來越大,女性平均為33歲,男性平均為35歲。
英國婚姻基金會專家哈裏·本森説,結婚率下降的趨勢對孩子不利。他認為,婚姻不是萬靈藥,但在維持家庭穩定方面更有效。英國近一半青少年沒有與親生父母生活在一起,因為其中不少孩子的父母從未登記結婚,生下孩子後彼此分開。
美國婚姻顧問伊恩·克納注意到,過去10年間,美國人婚姻從“浪漫式婚姻”逐漸向“陪伴式婚姻”過渡,人們擇偶時越來越願意找能成為“最好的朋友”的伴侶,而不是“激情”伴侶。(文中受訪對象均為化名,實習生閆柳瑾對本文亦有貢獻)
之二:“預製菜化”的速配式婚戀
張楠楠
傳統情感關係是從普通朋友逐漸水到渠成轉向伴侶,但這種發展過程在“雲相親”中並不適用。伴隨媒介技術嵌入,“雲相親”青年從擇偶要求、相親篩選、關係建立到情感維護,呈現出績效化、程序化、效率化、標準化流水線式作業等特徵,情感關係普遍存在“即烹即配”的“預製菜化”現象。

“雲相親”三步走
“雲相親”第一步通常是將擇偶要求標準化。在&&上,只需花費很短的時間就可以了解對方的基本情況,將所有信息轉化為可以量化的指標,為對方的相貌、工作、收入、家庭、學歷等打分。
第二步,對擇偶候選人進行篩選,判斷是否有必要進行深入了解。有人總結了一套相親鐵律:“約會中如果對方提前縮短流程直接pass(略過),聊天中敷衍回復或很少主動延伸、開啟話題直接pass。”雙方都按照某種約定俗成的標準進行判斷,以類似績效考核的方式給自己設立計劃目標,也對另一方進行考核評價。如能順利“過五關斬六將”,即向準親密關係靠攏。但這種“預製菜化”情感關係,真實的情感基礎比較薄弱。
第三步,“預製菜化”情感關係的理性維護。有青年談到“周末基本都會出去約會,但很清楚是為了結婚而去的”“別人都説這種行為算‘海王養魚(指多線發展)’,但我並不認同,到了這個年紀時間很寶貴耽誤不起,只是為了提高效率,最終能走到一起的才是真愛”“我不想獨自一人,但更不想被糾纏、束縛,想要能隨時抽離的自由”。

困在追尋完美伴侶的游戲中
追求靈魂伴侶是人性自然驅使的産物。一些線上&&恰能提供海量用戶、列出清單任君挑選,就像想買新衣服時會得到新産品的目錄一樣,但極可能貨不對板、注水嚴重。
相親者此山望著彼山高,甚至可能會克制、疏離情感的發展,不自覺地認為下一個選擇可能會更好。看似一時愛得難解難分的關係,可能沒有任何信號就突然化為泡影,“斷崖式分手(指突然不&&)”往往和“快餐式愛情”相伴隨行。
在技術支持下,用戶認為無須過多耗心耗力,就能找到條件更好的伴侶,這恰好契合了部分&&的運營邏輯。作為服務的提供者,&&如何提升用戶黏性是盈利的關鍵。相親交友類&&與其他類型服務有所不同,並不是越好地提供針對性服務、滿足用戶需求就能有效提升用戶粘性,相反,如果使用戶迅速完成擇偶匹配,則會導致用戶流失。
因此,&&往往會討巧地借助這套商業規則,讓用戶感知到&&一直擁有潛在的優質相親交友對象。用戶的這種心理作用與&&提升用戶粘性的目標不謀而合。因此,&&就會不斷吸引用戶嘗試更多的快餐式愛情,最終把用戶困在追尋完美伴侶的游戲中。
警惕技術發展對青年婚戀的衝擊
部分“雲相親”青年開始接受這種“預製菜化”的情感關係,但不會在這段關係中毫無保留地付出真心。他們在內心深處並不認為這種游離的情感關係可以與長期的親密關係或是真愛畫等號,彼此間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不會花費更多精力維護,是偏向娛樂式的、淺嘗輒止的關係。由此,“戀愛降級”“愛情平替”等在社交網絡上成為熱詞。
從這一角度看,媒介技術為相親青年提供了進攻和退守的空間。至此,“預製菜化”的情感關係似乎使得愛情的意義被消解。這打破了我們以往對情感關係的認知,以愛情為基礎的情感關係在技術飛速發展的理性社會中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而真正意義上的親密關係或將逐漸成為這個時代的稀缺品。
技術嵌入已部分取代傳統情感關係實踐,不僅對青年,甚至對整個社會的情感認知産生了深刻影響。應對技術的挑戰,關鍵在於幫助青年群體樹立健康的婚戀觀,正確認識、合理使用技術&&,避免陷入追尋“預製菜化”完美伴侶的游戲。(作者係華中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生導師)
之三:“左滑右滑”的愛情游戲
張睿
有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6月,超過3000萬的中國互聯網用戶在婚戀交友&&上追尋愛的可能。然而,在看似海量的選擇中,真正能建立持久親密關係的寥寥無幾。這背後,不僅是一場數字化的愛情游戲,更是關於現代人情感困境的深刻反思:在一切皆可“左滑右滑”的時代,我們對愛情的理解和追求,隱藏着哪些不為人知的情感邏輯?
打造相親網絡人格
假使你即將開始一場網絡相親,首先你得在這個虛擬世界裏“打造”自己的個人主頁,以便訪客一目了然查看個人信息。例如,“關於我”“興趣愛好”“感情觀”“心儀的TA”“MBTI性格類型”等,就像在超市裏給自己貼上標籤。每個人被簡化為一系列屬性,通過選擇性展示具有市場價值的信息,如家庭背景、工作及學歷等,個體變成了可以被量化、交易和競爭的“商品”。
儘管每個人都努力展現自己的獨特性,最終卻不約而同變得千篇一律。大多數人在描述自己時使用的形容詞幾乎一致,比如“我可愛有趣所以才單身”,女性強調“溫柔體貼”“喜歡兒童”,男性則強調“收入穩定”“房車財産”。這種環境下,尋找伴侶的過程更像是在市場中挑選符合特定標準的商品,而不是尋找具有深度和獨特性的人。

變味的“喜歡”
&&採用算法每天為用戶匹配潛在伴侶,通過內設聊天窗口、速配小游戲等推動互動産生。這些設計塑造了一種特定的情感邏輯,影響了用戶的情感選擇、表達、節奏和期許。
傳統相親方式通常需要經過長時間的觀察和理解才能做出選擇,而在網絡環境中,僅需一次左滑或右滑就能決定這個人是否從此在你的世界中消失。這種快速選擇過程將決策變成了一種快速消費行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通常將愛人視為不可替代的獨特存在。然而,在數字化情感世界中,由於潛在候選者眾多,我們容易陷入一種觀念,即每個對象都可以被其他人替代,情感在不斷比較和權衡中受到抑制。
傳統上“喜歡”被視為一種親密關係的標誌,具有排他性和相互性。然而,在網絡相親&&中,“喜歡”按鈕被賦予了新的含義和功能,成為可累積、兼容、切分、無限生成的事物。用戶可根據自己的篩選標準,短時間內向多人表達“喜歡”,或在某個時間段內持續獲得他人“喜歡”。這種模式讓原本嚴肅的親密關係異化為一場手指滑動的游戲。有人“喜歡”所有的人以增大配對機會,有人則沉醉於收穫大量“喜歡”的滿足感,以此看作是衡量自我魅力的量化游戲。
對效率的追求誕生了速配相親模式。以青藤之戀的“五分鐘巴士”為例,這裡的情感交往就像是流水線作業。你和每個潛在伴侶有5分鐘時間聊天,時間一到,就像按下了暫停鍵,談話立刻停止。繼而你可以做出選擇:是繼續深入了解,還是換個頻道,看看下個人會是誰。每天晚上,你最多可以經歷6場這樣的快速約會。
這種模式下,很多用戶開始實行“標準化”社交——就像電話營銷,每次都在重復相同的&詞。這種大規模、高效率的互動,雖然聽起來很吸引人,但可能讓真正的情感聯結變得更加困難。

公交司機劉艷明佈置婚禮巴士 張楠 攝
破局的契機
&&的競爭力依賴於“優質用戶池”,並利用這些“優質用戶”的高強度曝光作為吸引新用戶的關鍵資源。具有學歷、職業、收入等方面優勢的用戶,往往以各種方式被&&流量予以傾斜。在這樣的場域中,人們越來越專注包裝自我,而非真實的親密互動。
在高效的篩選與低轉化率之間,很多人深受“等待”的煎熬。隨着使用時長增加,很多用戶積極營業的心態被消磨,而“被拒絕”的體驗頻率之高、感知之直接,讓用戶不得不消耗巨大的情感能量來維護自己的心態。顯性的拒絕包括“對方對你無感”“對方認為你不合適,已取消喜歡”等回復,隱性的拒絕則包括突然中斷聊天等五花八門的形式。等待緣分成為權宜之計,既成為心靈寄託,也在逐漸催生心態的崩壞。
儘管冷親密現象標誌着在線戀愛與尋求伴侶的過程遭遇了困境,但實際上,這也為我們提供了破局的契機。關於情感生活和親密關係的討論空間,具備推動理性對話、引發新的社會共識、創造新的情感模式的潛力。
我們始終相信,建立真實深入的情感連接仍是可能的。我們需要重新定義和塑造我們的情感紐帶,以適應這個正在變化的世界,一同在情感生活的“冷化”中尋找溫度。(作者係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
之四:“劇本殺相親”因趣結緣
程曉莉
劇本殺從熟人圈延伸到陌生人社交中,一度成為城市青年,尤其是“Z世代”社交破圈的新形式。相親劇本殺正是新型複合消費業態之一,這一活動類型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南京等城市逐漸流行開來,受到青年群體青睞。

青年人在體驗沉浸式劇本殺
邊“玩”邊相親
新生代青年希望在收穫浪漫愛情的同時,兼顧資源匹配和經濟理性需求。傳統一對一相親形式較為固定,成本也較高。喝咖啡或吃飯是相親較為普遍的形式,少則一兩百、動輒四五百的相親成本,對青年而言是不小的經濟負擔。他們追求“小而精”消費,也偏好新奇、時髦的消費活動,尤為注重“玩”在日常生活中的價值。此外,時間成本也是新生代青年相親中重要的考量要素。周末是極為珍貴的閒暇時光,他們追求周末時間使用效率的最大化和行為的高密度,希望在更少的時間內完成更多事。
劇本殺具有以游戲互動為主的鮮明社交屬性,一定程度上構成了“趣緣部落”,尤其吸引以趣緣為社交取向的青年。與其他社交媒介相比,劇本殺具有強故事性。組織方精心挑選了具有趣味性的劇本,且每種劇本的場景和玩法不同,參與者可以自由選擇劇本進行組合。情節的未知感、角色代入感都為參與者帶來沉浸式的游戲體驗。參與者彼此以劇情賦予的虛擬角色展開互動,並自發建立活動秩序。每個參與者都是游戲的一部分,合作推理、共同創造的游戲機制讓參與者的游戲體驗超越個人性並走向整體性,彼此之間形成高度的情感連接,這有助於推動親密關係的快速建構。
“先游戲後自我介紹”的活動流程,為參與者提供了更輕鬆自由的社交空間,打破了現實世界中的身份壁壘。參與者暫時從職業、身份、地域等符號中抽離,以平等玩家的身份進入游戲。在沉浸式的游戲氛圍中,他們通過角色扮演、邏輯推理和話語表達,較快速地熟絡起來,並初步了解各自的性格,形成對他人的初步印象。通過游戲破冰之後,成員之間開始較為深入地交流,話題也從虛擬的游戲延伸到現實社會中。在熟人圈層,青年群體往往會將自己的情感經歷和婚戀焦慮以雲淡風輕的方式隱藏起來,但在非熟人圈層、利益無涉的陌生人組成的活動中,關係的匿名性和短暫性使他們更加敞開心扉,也更容易進入到親密關係之中,表達自己的情感需求。在游戲間隙,參與者如同好友一般分享各自的情感經歷,講述面臨的婚戀壓力,形成惺惺相惜的情感共振。

《戀愛心理學》課程組組織學生開展課程實踐,通過系列團建活動幫助學生認知自我、認識他人
為青年擇偶實踐賦能
活動結束後,參與者們會再次評估活動過程,啟動深入接觸方案,通過互動體驗、容貌水平、背景信息來綜合審視他人,進而篩選可以深入接觸的對象。為了節約時間成本,青年多直接詢問對方的意願,並將聊天和見面看成流程式的操作。為規避因活動中憑“感覺”“眼緣”的印象與實際産生偏差,多線接觸成為參與者普遍的行動策略,甚至成了默許的潛規則。青年對接觸對象進行量化的審視甚至打分,在比較中不斷權衡。只有當他們與某個對象達成確定性交往時,多線接觸才會終止。
相親劇本殺為青年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擇偶媒介,一定程度上為青年的擇偶實踐賦能。作為去中心化和去紅娘化的相親形式,相親劇本殺的活動形式迎合了城市青年群體社交孤獨和婚戀焦慮的雙重情感困境。組織方以標準量化為導向的篩選機制節約了相親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集體相親形式為青年提供了效率更高的擇偶通道。
在社會轉型期傳統與現代婚戀觀交織下,青年既追求交往安全,又渴望情感自由。低成本和高效率的相親模式為青年提供了廣闊的擇偶空間並製造出短暫的歡愉。但值得注意的是,歡愉過後,淺層的情感聯結仍難以轉化為長遠、穩定的親密關係,甚至加劇了青年的空虛感和孤獨感。
當前社會,“母胎單身”和大齡剩男剩女等社會現象較為普遍。參與相親劇本殺活動正是城市單身青年群體對生存困境和婚戀壓力的主動回應,也反映了在原子化的現代社會中,青年人際之間情感疏離且社會支持不足的事實。青年群體應增強安全意識和合理的消費意識,尋求健康的情感需求滿足通道,樹立健康的擇偶觀,理性把握內心節奏與加速社會、消費主義與情感之間的關係。(作者係江蘇開放大學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