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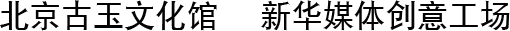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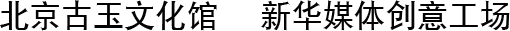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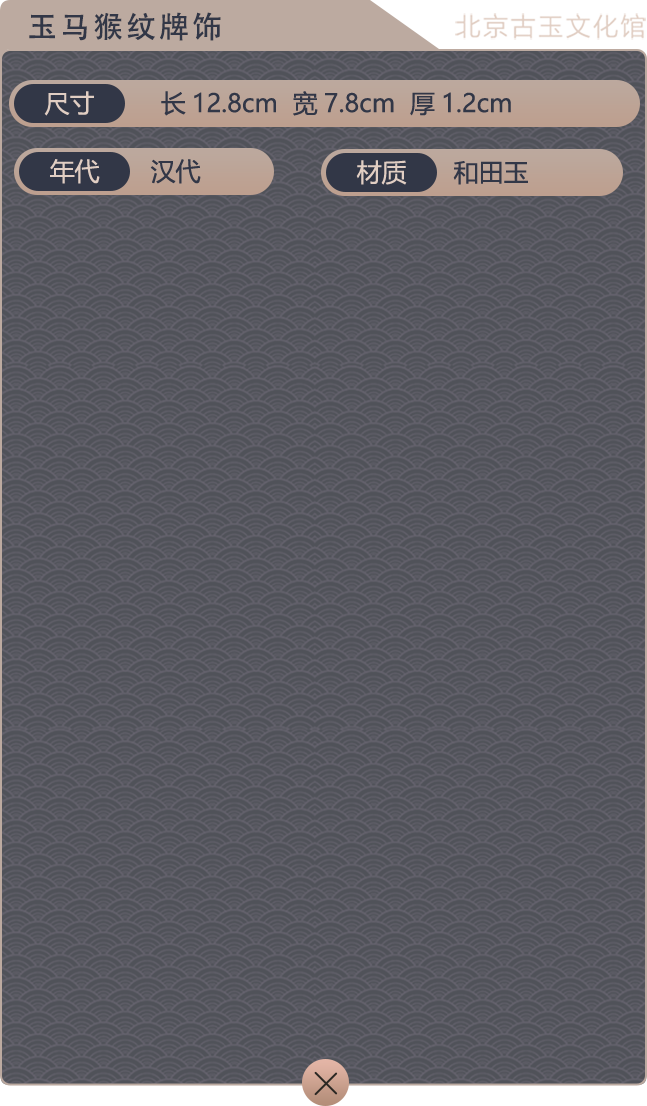
北京古玉文化館藏有一快玉牌飾,長12.8cm,寬7.8cm,厚1.2cm。它是由和田玉淺浮雕完成。其年代為漢代。
這件作品的藝術性很強,雖然是寫實手法,但非常簡潔明快,以及其簡練流暢的線條,生動勾勒出猴子騎坐馬上。它以馬身省略,凸顯馬的頭部來體現馬昂首嘶鳴的形象。
猴,生動活潑、富有靈性,深得人們喜愛,在中國民間具有深厚的文化意蘊。作為十二生肖之一,它與吉祥運氣相連,深入人心,常見於小説、繪畫,以及民間建築雕刻中。
中國人對猴子和馬的關係,有一種奇特的習俗和觀念:在馬廄中放置猴子,靠猴子的自由跳動來驚擾馬匹,認為這樣馬就不會得病。古代文獻中,也有許多關於猴子與馬在一起就能防止馬匹不得病的觀念的記載。如:《五雜俎》、《搜神記》、《四時纂要、《夷堅志》、《虎鈐經》、《猗覺寮雜記》,都有相關記載。
猴子和馬的複合形象在我國最早出現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寧夏、內蒙一帶。二十世紀初,西方人赫定在新疆和田約特幹也採集到一件猴子騎馬的陶俑。這些地方氣候大多不適合猴子生存,為何猴子的形象卻會在這裡出現,並且是和馬組成一個飾件或一幅畫面?
日本人石田英一郎認為:“從猴子本身生物學上的分佈情況來看,或從它在宗教信仰當中所佔地位來考慮,這種思想的起源,恐怕是在由日本、中國、印度組成的圈內,即在猿猴分佈最多而猿猴宗教崇拜的中心地域的印度”。印度古文獻《梨俱吠陀》、《摩柯婆羅多》、不空譯《摩柯僧袛律》中,也都有猴子和馬關係的敘述。這些記載證明在印度的佛陀或更早的時期,就有了猴子與馬的複合觀念,並且已經産生了猴子能給馬治病的複合觀念。
後來,這種觀唸經過斯基泰或其他草原民族傳播到了我國的新疆、寧夏和更遠的鄂爾多斯草原。猴子和馬這一形象的功能正好符合我國北方草原民族以馬為伴的生存狀態。於是,這裡的草原民族通過這一形象來祈求自己的馬匹無災無病、膘肥體壯。
另一方面,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在新疆和田約特幹發現的猴子騎馬陶俑正好填補了印度和中國大陸之間傳播當中的媒介方面的空白。猴子在新疆這裡本無法生存,所以,只能説其形象的出現是出於圖像上或者觀念上的傳播。
猴子和馬這一組合形象及其附屬功用不僅在我國北方草原地帶流行和傳播,後來也通過北方草原文化又帶到了中原農耕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相結合。這一切,在許多漢代出土文物中,都得到了有力印證。
甘肅金塔縣漢代居延肩水金關遺址出土木板畫、四川成都曾家包出土東漢畫像石墓、河南密縣打虎亭一號漢墓南耳室西壁石刻畫像、陜西綏德四十里鋪漢代畫像石、陜西管莊、白家山、賀家灣、四十里鋪等地出土畫像石等文物上,都有相關題材的表現。
上面所提到的圖像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馬匹都被拴在馬廄中或樹上,並且旁邊有一隻猴子。這些畫面與我國古代文獻中記載的有關猴子給馬能治病線索,非常吻合,因此,畫面所反映的寓意,就是猴子能給馬治病這一觀念。
另外,“猴”與“侯”,“逢”與“封”的諧音關係,使其造型又&&了“馬上逢(封)猴”的寓意。秦漢時期,漢、匈之間經常發生戰爭,騎兵大行其道,《史記·陸賈列傳》陸賈對漢高祖説:天下可“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就是證明“馬上”為馬背之上的含義,寓指在馬背上建立軍功而封侯。而早在商、周時期就有公、侯、伯、子、男爵位的稱號。所以,漢代出現“猴”、“馬”形象的文物,其寓意之一就是通過武力征伐,在“馬背上”建立功勳,進而封侯晉爵。這就是猴子和馬這一題材藝術所包含的信仰觀念的一次轉變。
由此,我們就可以省察北京古玉文化館所藏這件猴馬組合的玉雕作品,它所反映的文化內涵和它的淵源之久遠了。
不管是猴馬造型最初的寓意,還是後來寓意的轉借,都是一種人類對美好未來的嚮往,猴子給馬治病是希望馬能更好的為人類服務,同時也顯示了古代人類淳樸的思想。